蔡元定乐律理论研究
南宋蔡元定是中国古代较有影响的乐律学家,他因创研了较为实用的改良律制三分损益十八律(十二正律加六变律)——而著名。他的著作《律吕新书》是隋唐以后第一部较为系统全面阐述乐律方面的音乐理论专著。后人为该书补遗、释义。评注的不乏其人,可见影响之大。但他有关燕乐调的理论专著《燕乐原辩》(《宋史》又谓《燕乐书》)已散失不全,《宋史》中所辑录的文字又过于简扼,给予后人留存的疑点较多,直至今日研究者甚多,讨论仍然非常热烈。

蔡元定画像
南宋大理学家朱熹曾说:“吾友建阳蔡无定季通“......独心好其说而力求之,旁搜远取,巨细不捐,积之累年,乃若冥契,著书两卷,凡若干言,予尝得而读之,爱其明白而渊深,缤密而通畅,不为牵合傅会之谈,横斜曲直,如珠之不出于盘。”给予蔡元定极高的评价。
蔡元定的理论本于传统,又有创见,确是古代音乐理论一大家。然而对于他的理论历来褒贬不一,议论多有偏颇。包括笔者在内,对于他的认识也是随着再三细读他的著作而得以改变。以下只是笔者的学习点滴心得,有臆会之处还望专家同仁批评指正。
夹钟为律本说
燕乐“独用夹钟为律本”是蔡氏《燕乐书》中阐述“收四声之略”的一段结语,曾引起不少学者的注意和探讨,解释多样,也属于乐律学史研究当中的一个疑点。
类似的说法最早有《新唐书》的“凡所谓俗乐者,二十有八调:......宫调乃应夹钟之律,燕设用之”一说。关于俗乐二十八调比较完整的记叙,要数唐段安节《琵琶录》为首,但论及俗乐调律高的,还是《新唐书》为早。其次尚有北宋沈括的《补笔谈》“盖今乐高于古乐二律以下,故无正黄钟,只以合字当大吕,犹差高,当在大吕、太簇之间。”一说比较具体。在这段律高的比较中,“古乐”及“黄钟”,当指唐天宝十三年前后期间的律高。据天宝时太常寺石刻所录,时号越调,为唐新律黄钟均之商(太簇),而沈括说在大吕与太簇之间,近太簇,说明北宋俗乐的教坊律,不比于唐新律之太簇律。
《新唐书》所说俗乐应夹钟之律,与沈括所说的内容不相干。《新唐书》虽出于宋人之手,但讲述的立场和背景不同,关于俗乐的律高比较对象也就不同。《新唐书》是以中唐以后的律高与唐初的律高相比,即中唐的黄钟相当于唐初的夹钟。而《补笔谈》是以北宋沈括「所在时的俗乐教坊律,与中唐后所用的太常律相比。从太常寺石刻所记述的俗乐调名与律名的关系来看。当时雅、俗乐只用同一律高标准。
蔡元定所说“独用夹钟为律本”,与以上两例的律高标准的比较含义都不同,他并非在谈论俗乐的律高标准问题。这段文字出现在“收四声之略”一段中,无疑与收声(住字、杀声)的议题相关。
“收四声”在宋代讲的是俗乐四询同住音犯调问题。有关调相犯,沈括《补笔谈》中还有“外则为犯”一说,给“犯”义作了界定,又说有“祖调、正犯、偏犯”等几种犯调形式继后陈肠《乐书》有说:“五行之声,所司为正,所敬为旁,所斜为偏,所下为侧。如正宫之调,正犯黄钟宫,旁犯越调,偏犯中吕宫,侧犯越角之类。”所谓旁、偏、侧,是由新调的宫位与原调宫位之间的方位与距离而定义的。这一点比起沈括所说更为详细。陈肠的正犯说并不出沈括的“外则为犯”的范畴。
然而,姜夔在歌曲《凄凉犯》序中却说:“凡曲言犯者,谓以宫犯商,商犯宫之类。如道调曲申犯双调,或于双调曲中犯道调,其他准此。”

行书《凄凉犯》
他完全排斥了十二宫之间的犯调手法,认为“十二宫所住字各不同,不容相犯。十二宫特可犯商、角、羽。”雹弯可见姜夔的犯调说是限定在更小的范围,即同住音犯调。
蔡元定在《燕乐书》中“燕乐以夹钟收四声”一段中说:
“曰宫、曰商、曰羽、曰闰,闰为角;其正角声、变声、微声皆不收,而独用夹钟为律本。”
大意是:燕乐若以夹钟律位为调杀声位的话,只能是某调的宫音、某调的商音、某调的羽音、某调的闰音,不能是其它的音。闰音是充当着角调的杀声,正角音、变音、微音是不能作杀声的。这些调在一起相犯的话,收声只能建立在夹钟律上。这就是南宋学者一律四犯说的典型理论,显然与北宋的学说稍有不同。不过,蔡元定并未像姜夔那样正面提出反正犯说。
以夹钟收四声,或以夹钟为律本,只是以夹钟为例,来阐述同律同住音相犯的理论,并非在理论律高标准的问题。所以说他只是例举,因俗乐二十八调在宋教坊律的对应关系中,夹钟律下根本就没有四个调可犯的。它只可能建立高大石调与中吕宫二个调的对置,即使在中唐新律的仲吕律下,也还是只有这二个调。不过蔡元定也并未限定在同律下必须四犯,而不能二犯、三犯的,更没限决同住音犯调必须在夹钟律下进行。因此,这仅仅是例举。
同住音相犯的手段自古早有之。刘安《淮南子》所说的“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为六十音”;“以十二律应二十四时之变,甲子、中吕之微也,丙子、夹钟之羽也,戊子,黄钟之宫,庚子,无射之商也、壬子,夷则之角也……”此类左旋的旋宫法都属同住音相犯的范畴。
蔡元定的同住音相犯的旋宫主张,并不限于俗乐的调发展中。他曾在以雅乐研究为中心的“律吕新书》中,不厌其烦地详细列举了六十个调及其每调七声所用律位,而且是以每一律五调(同住音调)为一系列而排序的。他在(六十调图第九)的按语中强调了“黄钟宫至夹钟羽,并用黄钟起调,黄钟毕曲;一应钟宫至太簇羽,并用应钟起调,应钟毕曲”的调转换原则起调、毕曲都要用同一律,这与他的“独用夹钟为律本”的原则是一致的,只是用语不同而已。
沈括所说的“祖调”,就是犯调中的起始调,现代称原调。沈氏虽没用文字强调,在犯调中必须是同律同住音相犯,即起调、毕曲必须独用一律的原则,但他在为十二律配二十八调的排序中,也都是以调的杀声为同一“字”的方式而加以归纳排序的,并一一注明角调的变宫住字声位。可见蔡氏的起调毕曲说、律本说是承袭沈括的祖调说、杀声说。无论沈氏的祖调说或蔡氏的起调毕曲说,都不限定于夹钟律或仲吕律,这是明人所皆知的。
蔡氏的起调毕曲说,与《事林广记》中“八犯诀”所说的“七归祖......八归宗;南宋张炎《词源》中说的“归本宫”有相似之处。

《事林广记》
明朱载消也强调过起调毕曲的原则。他在《律吕精义》一文中说:“系宫调者,起调毕曲皆宫,韵脚或宫或微......系角调者,起调毕曲皆角,韵脚或角或羽”从韵脚一说,联系全段文字,说明朱氏谈论的是调式或制曲,而不是犯调问题。
就因为起调毕曲说有二种不同理论内涵,导致了元陈敏子等人对蔡元定的说法提出异议。陈氏在《琴律发微》中说:“古书中及五声十二律还相为宫六十调者虽多,独于制曲起毕之说鲜及之。惟西山蔡氏......其说日黄钟宫至夹钟羽,并用黄钟起调,黄钟毕曲......由是观之起调毕曲皆须本律琴家于起调多无定准......凡制调引曲,其第一声皆合本律声,然古今所制多杂用本宫诸律声。”清凌廷堪及(日)林谦三对蔡元定的说法也作了专题评论,他们在理解上与陈氏相同。凌氏在《燕乐考源》中的评价是“附会”;林氏在《隋唐燕乐调研究》,却认为,蔡元定的每一曲第一声全用调主音的主张,带有“理想论”的色彩,但决非“空论”。他还列举了一些古代传谱作统计,以此想证明蔡元定的“同律起毕”理论是有一定根据的。可见陈、凌、林等氏的误解之深。
这里的“黄钟起调”,怎能理解为乐曲第一个音要用黄钟,如何用音是个制曲问题蔡元定这里是在理论六十调的关系问题,他用一律五调分组排列,并详细列出每组各调所用阶音的异同,显然是在谈与旋宫犯调有关的包括同音异律等一系列问题。所谓黄钟起调、黄钟毕曲,是蔡元定针对黄钟宫、无射商、夷则角、仲吕徽、夹钟羽这五个同住音调之间,在相犯时所要遵循的原则而言的。看来,对于以上陈、凌、林等氏对蔡元定的这些批评,还得重新评估。
还有一个值得我们要注意的问题,当这五个调的住音都在同一个律下时,只要用其中一个调开始,其中一个调结束,都是符合这个原则的,因蔡元定并没注明一定要用起始原调作为结束调。
从《事林广记》四犯中:宫角羽商、商羽角宫、羽角宫商所列举的三种同住音犯调模式来看,强调的也是同生音,而不是归本宫(调),也即不一定要回原调。这一点,与蔡元定的理论是相应的。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感谢每一位辛勤著写的作者,感谢每一位的分享。

相关资料

- 有价值
- 一般般
- 没价值








24小时热门
推荐阅读


关于我们

APP下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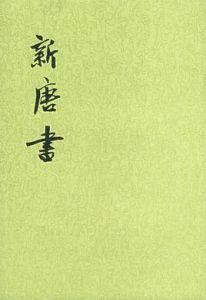












{{item.time}} {{item.replyListShow ? '收起' : '展开'}}评论 {{curReplyId == item.id ? '取消回复' : '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