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益主义
发展历史
早在效益主义正式成为哲学理论之前,就有效益主义思想雏型,例如享乐主义以及后果主义出现。公元前5世纪的亚里斯提卜( Aristippus )、前4世纪的伊比鸠鲁提出了享乐主义( Hedonism )。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是最高的善。奥古斯汀( Saint Augustine )提出幸福是人类欲望的终极。托马斯·阿奎那( Thomas Aquinas )也曾深入探讨关于幸福与快乐的问题。
后果主义的思想在中国萌芽于春秋战国之交。当时的墨家学说提倡社会道德意义上的善,包括政治稳定以及人口、财富的增长。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政治学学者( Niccolo Machiavelli )也认为国家的行为无论残暴或仁慈,都应服务于社会整体利益。
近代英国哲学家与伦理学家如坎伯兰( Richard Cumberland )、弗朗西斯·哈切森与大卫·休谟都有效益主义的倾向。据边沁指出,他在英国化学家约瑟夫·普利斯特里、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 Claude-Adrien Helvetius )、意大利法学家贝卡里亚( Cesare Beccaria )以及休谟等的著作中都发现了效益主义的身影。休谟在《道德原理研究》中写道:
“在所有的道德判定中,人类的总体效益都应当是最重要的因素。不论是在哲学还是在现实生活现关于责任界限的争论,最确凿可行的解决途径都莫过于从所有方面确定这种责任界限对人类整体利益的影响。如果任何错误的观点在表象的伪饰下得以流行,只要更深入的经验和更可靠的理性赋予我们关于人类行动更正确的理念,我们就应摒弃最初的观点,重新划定善与恶的道德界限。”
休谟师从弗朗西斯·哈切森。事实上正是哈切森引入了一个重要的功利主义思想。在《美与美德观念的起源研究》中哈切森指出在选择最为道德的行动的过程中,美德与特定行为所能造福的人的数量成正比。同样的道德上的罪恶与特定行为殃及的人的人数成正比。至善之举就是能够促成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行动,极端的也就是导致最大痛苦的行为。
在此书的前三版中,哈切森论及多种计算任何行为的道德性的数学算法。他的思想启发了边沁的“幸福总和”思想。
有人认为约翰·盖伊提出了效益主义伦理学的第一套系统理论。在《论美德或道德的根本原则》一书中盖伊说道:
“快乐,个体的快乐,是人类行为合理且最终的目的。每个特定行为都可以被说成是具有合理而独特的意义。但是它们仍趋于或应当趋于某种更深远的事物。由此可以显然地得出人可能问及并期待追求任何一者的原因:现在诘问任何一种行为的原因,只是穷究它的目的,但是期待最终目的的原因或目的就无疑是荒谬的。追问为什么我追求快乐,得到的答案只能是对快乐这一术语本身的解释。”
对幸福的追求被赋予了神学基础:
“上帝具有永恒的内在快乐并且依据他的至善创造人类使得以下事实变得确凿:人类除了被设计成追求快乐的生物之外没有其他可能。也即,上帝愿人类幸福并设计了人类的幸福。因此我的行为,只要能增进人类的幸福,就应受肯定。因此,既然上帝的意志是美德的直接准绳,人类的幸福又是上帝的意志的标准,那么人类的幸福就可以被说成是美德的标准。我将会尽自己所能增进人类福祉。”
盖伊的神学功利主义被威廉·帕雷( William Paley )发展并普及。帕雷被认为不是一个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他的哲学专著主要是对他人思想的整合并且适合学生学习而非学术讨论。但是,他的《道德与政治哲学原理》是剑桥大学的必读书籍并在美国的大学中有相当影响力。
效益主义正式成为哲学系统是在18世纪末与19世纪初期,由英国哲学家兼经济学家边沁和米尔提出。其基本理论是:一种行为如有助于增进幸福,则为正确的;若导致产生和幸福相反的东西,则为错误的。幸福不仅涉及行为的当事人,也涉及受该行为影响的每一个人。
19世纪末期的效益主义代表人物亨利·西奇威克( Henry Sidgwick )认为效益主义来自对“常识”的道德系统的反省。他论证多数的常识道德被要求建立在效益主义基础上。他也认为效益主义能解决常识学说的模糊和前后矛盾而产生的困难和困惑之处。在20世纪效益主义虽然经过摩尔( G.E. Moore )的批判,但英美哲学家与英国自然科学家兼伦理学家图尔明( Stephen Edelston Toulmin )、牛津大学的诺埃尔-史密斯( Patrick Nowell-Smith )、厄姆森( J.O. Urmson )以及澳大利亚的斯马特( J. J. C. Smart )等人仍为效益主义辩护。
主要概念
效益主义认为人应该做出能“达到最大善”(即“最大效益”)的行为,所谓最大善的计算则必须依靠此行为所涉及的每个个体之苦乐感觉的总和,其中每个个体都被视为具相同分量,且快乐与痛苦是能够换算的,痛苦仅是“负的快乐”。不同于一般的伦理学说,效益主义不考虑一个人行为的动机与手段,仅考虑一个行为的结果对最大快乐值的影响。能增加最大快乐值的即是善;反之即为恶。边沁和米尔都认为:人类的行为以快乐和痛苦为动机。米尔认为:人类行为的唯一目的是求得幸福,所以对幸福的促进就成为判断人的一切行为的标准。
效益主义派别
效益主义根据应用的方式可分为以下几种:
行为效益主义( act-Utilitarianism )
规则效益主义( rule-Utilitarianism )
普遍效益主义( general-Utilitarianism )
行为效益主义在探讨一个行为的对或错时,会以“当下该行为”是否能产生最大效益来进行判断。而规则效益主义则认为人们若能因为遵守某种规则而达到最大效益,则遵守该规则就会是对的行为,反之,违反该规则则是错的。
单就闯红灯为例,行为效益主义可能会认为“当下”闯了红灯可以节省时间并减低怠速排放的废气,故在遇到红灯且保证不发生时应该闯红灯,如此才能达到最大效益;但若以规则效益主义来看,如果每个人能够遵守交通规则则能大大降低的发生概率,因此遵守交通规则才是合乎伦理规范的行为,我们不应该闯红灯。
再以说谎为例,行为效益主义会先计算说谎后所带来的结果是否达到最大效益,如果说了谎可以达成最大效益,则当下的说谎行为是可以接受的,例如:对歹徒说谎最后使他被捕。但若以规则效益主义来分析,如果人们都无法诚实的据实以告,则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会充满猜疑,最终人们会不信任彼此,故无法达到最大效益,因此诚实是我们应该遵守的规则,说谎是不符合伦理规范的。
有人 认为,普遍功利主义和规则功利主义本质上都属于情境功利主义的一种。
应用
效益主义的影响甚为广泛。它在法律、政治学、经济学方面更有特别显著的重要性。例如在惩罚方面,效益主义反对“一报还一报”的“报应论”。效益主义者认为惩罚的基本原理是通过改造罪犯或保护社会不受罪犯破坏,从而避免发生更多的犯罪行为,同时也使其他人因惧怕受到惩罚而不敢犯罪。在政治哲学上,效益主义者赞成将民主作为使政府利益与公众利益取得一致的一种方法。他们认为每个人的最大自由和其他人的同等自由是一致的。不过也有人因为强调政府利益的一面,而走向保守主义、甚至主义。另一方面,也有人因相信人性本善,认为最大的幸福是来自社会的根本变革,从而走向无政府主义的共产主义,如威廉·戈德温。在经济学上,所谓边际效用分析学派如威廉姆·斯坦利·杰文斯,则是从边沁那里吸取了许多思想,所谓“福利经济学”是以“比较爱好”代替“比较效用”,也表现了效益主义的基本精神。在经济政策上,早期的效益主义者倾向自由贸易,反对政府干涉。后期的效益主义者由于对私人企业的社会效率失去信心,又希望政府出面干涉来纠正私人企业的弊病。在当代的讨论中,人们对伦理学语言的分析,以及对边沁的“快乐计算”均已失去兴趣;效益主义出现了种种修正的和复杂的形式。
列车难题 这是最著名的效益主义的例子,假设有一列车正在高速行驶,你是此列车的车长。如果继续行驶,将会导致5人丧生。假若你换轨,便能救回该5人,可是又会导致1人丧生。如果是主张效益主义,便会选择换轨牺牲1人救回5人。
正名
效益主义( Utilitarianism )过去称作“功利主义”,是透过计算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来规范伦理。然而“功利”二字在中文含义里带有贬意,为避免旧有的刻板印象与先入为主的观念, 伦理学家 近年来 逐渐称呼功利主义为效益主义。
批判
效益主义的中心思想,即每个人都应该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促进幸福,并避免不幸,这看来是应予肯定的。但关键性的问题是:整个规范伦理学是否都可以根据这个简单的公式来分析。是否有超乎快乐与痛苦之外的价值值得重视。如何衡量一个人吃了巧克力之后得到的快乐比别人多、少或者一样?没有方法来计算得到利益,也就没有方法确定什么行为是道德允许的。所以快乐利己主义在某种程度上行不通。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感谢每一位辛勤著写的作者,感谢每一位的分享。

相关资料

- 有价值
- 一般般
- 没价值








24小时热门
推荐阅读



关于我们

APP下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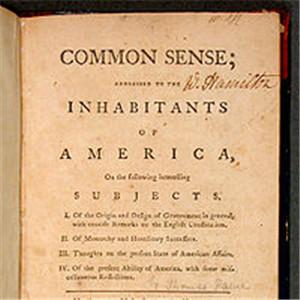












{{item.time}} {{item.replyListShow ? '收起' : '展开'}}评论 {{curReplyId == item.id ? '取消回复' : '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