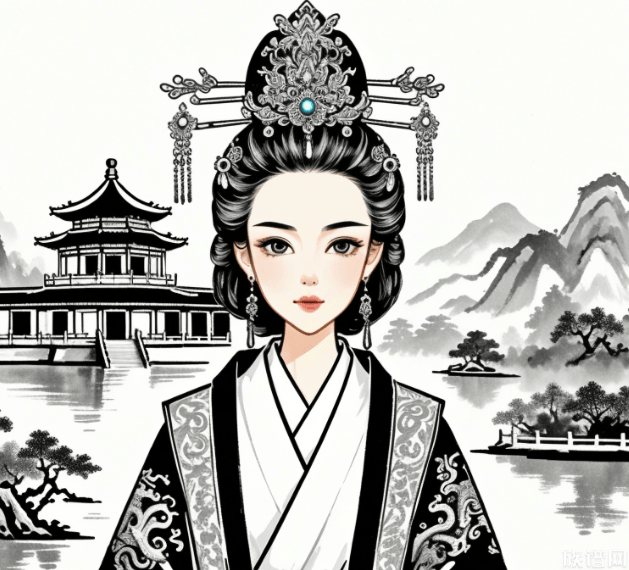齐鲁文化—齐鲁荟萃—从“述而不作”看儒家经典诠释的理论特质
正如哲学诠释学所指出的,理解是人之基本的存在方式。而不同文化共同体之间之所以出现不尽相同的理解形态,又与各文化共同体所具有的不同的精神特质有着直接的联系。本文拟从孔子倡导并身体力行的“述而不作”的叙述传统入手,从一个侧面对儒家经典诠释的理论特质作一探讨。
“述而不作”语出《论语·述而》,是孔子的自我评价:“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我于老彭。”其字面意思是仅传述既有内容而不进行创始性的工作。但事实上,正如孔子的有关工作所显示的,在他对既有内容的传述过程中实际上包含了创始性的义涵。正如朱熹所指出的:“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故作非圣人不能,而述则贤者克及。……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皆传之旧,而未尝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然当是时,作者略备,夫子盖集群圣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虽述,而功则倍于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这也就是说,孔子虽采取了“述”的形式,但却有着“作”的内容。因此,也可以把这种经典诠释方式称作“以述为作”。也正因为此,虽然孔子的有关工作在文本上的确是“皆传之旧”,但这并没有妨碍他成为儒家文化的开创者,成为推进中国文化完成由原初阶段向成熟形态转进的中心开启性人物之一。正是以“述而不作”的形式,孔子挺立了人的道德主体性,点醒了人们对作为自身内在本性的“仁”的自觉,为周初以来主要是作为外在行为规范的礼乐文化在人性本质的层面确立了内在根据,从而为中国文化发展成为以内在化的路向安顿人之生命意义为思想主题的成熟形态奠定了稳定的精神方向,实现了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根本变革[1]。
孔子所开创的这一传统对日后儒家经典诠释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一定意义上,“述而不作”成为了其后儒家经典诠释基本的形式特征。换言之,孔子之后,通过“传(贤)之旧”而进行传述和创作成为儒家经典诠释的基本形态。这一点在作为中国传统学术之正统的儒家经学中得到了鲜明的表现。就文体而言,构成经学的著述可分为“经”和“传”两类。就其本意而言,“经”指原创性的经典,而“传”则指诠释经文的著述。但事实上,在经学发展演进的过程中,人们把某些儒家思想奠基时代的传注之作也称之为“经”。如《春秋》是经,作为解释《春秋》的《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则是传。但至唐代,“三传”已被视为经。正是有见于此,清代章学诚指出:“今之所谓经,其强半皆古人之所谓传也。”(《文史通义·经解》)这也就是说,即使是对经而言,也有不少实际上是传而非经。不仅如此,在数量上经本身是少之又少的,即使到有宋一代,算上《孟子》,才合称“十三经”。而历代的传,则是成千上万,堪称汗牛充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文化传统中所谓经学,就是由一代又一代学人对为数极少的有限几本“经”不断加以传注、诠释而形成的。而传注、诠释的基本形态就是“述而不作”。这至少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经学的存在是以对作为“经”的原初文本的不断诠释为前提的,离开了对原初文本的不断诠释,所谓经学就无从谈起。
第二,尽管不能说在经学发展的过程中没有新的范畴与问题出现,但就其基本范畴如理、气、心、性、有、无、动、静、名、实、知、行等和讨论的基本问题如天人关系、心性之学、人性善恶、希圣希贤等而言,则堪称几千年来保持了显明的一致性,从轴心时代这些范畴和问题开始出现,到19世纪中叶西方近代文化传入中国之前,经学一直在围绕这些范畴和问题展开自己的学理系统①
第三,“述”成为儒家经学的基本叙事方式。不仅经籍成为经学阐释的先在文本、经学的基本范畴与问题一直与轴心时代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而且“述”而非“作”构成了儒家经学一以贯之的基本叙事方式。儒者在进行经典诠释时,往往是在经过“小学”功夫即对原典字词的训诂、考据之后,才进入义理的阐释。而在义理的阐释中,又往往要先溯其原始、再明其流变,并蒐集前此的各家注疏,最后才有所谓“断以己意”。这就形成了儒者皓首穷经,为一字而释数十万言,但其中绝大部分篇幅都只是“述”,而“作”者即阐述释经者自己意见的内容却只有数千言、数百言乃至数十言的情状。
第四,正如孔子之自述所表明的,在传统经学中,即使对“作”而言,人们也要自觉不自觉地采取“述”的形式。这至少有以下两种情况。其一,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无论是“述”还是“作”,立言的准则都是“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作为阳明后学中颇具批评反省精神的李贽对此有着颇为清楚地描述:“前三代吾无论矣;后三代,汉唐宋是也。中间千百余年而独无是非者,岂其人无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这种状况的结果是“人皆以孔子为大圣,吾亦以为大圣;皆以佛、老为异端,吾亦以为异端。人人非真知大圣与异端也,以所闻师父之教者熟也。师父非真知大圣与异端也,以所闻儒之先教熟也。儒先非真知大圣与异端也,以孔子有是言也。……儒先臆度而言之,你师沿袭而育之,小子蒙聋而诵之,万口一词,不可破也;千年一律,不自知也。”(《续焚书·题孔子像于芝佛院》)李贽的批评或有过激之处,但的确可以从一个侧面窥见经学立言“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的情状。其次,即使真有与先圣前贤不尽相同的“己意”,为了突显其存在的合法性,人们也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将之归结为与先圣前贤的明确论断或微言大义一致,从而事实上是给“作”披上了“述”的外衣。作为中国哲学史上重要发展阶段的魏晋玄学和宋明理学的开创者之一,王弼和周敦颐显然可以看作是中国哲学史中的“作者”。但其撰述却是以《周易注》、《老子注》和《太极图说》等传注的形式出现的。从“理存于欲”出发将倡导“存天理,灭人欲”的宋明道学指认为是“以理杀人”的清儒戴震在儒学发展史上无疑有其思想的独特性,但他确立自己有关观念之合法性的方式却是通过撰著《孟子字义疏证》而力图证明自己的有关思想是符合孟子的“微言大义”的。也正因为此,在中国哲学史上,甚至出现了将自己撰著的书稿托名于古人的情况,由此而有如《列子》等被今人悬疑为“伪书”的一类典籍。
儒家经典诠释的这一特征和西方文化与哲学在发展演进中所体现出来的诠释传统形成了鲜明对比。概而言之,如果说儒家经典诠释更为注重“述”,那么西方诠释传统则更为注重“作”。不仅如此,在“作”的过程中,西方文化在不同思想家的理论系统之间不是更为注重相互之间的承继关系,而是着力于突显自身不同于其他思想系统的理论特质,甚至不惜为此而对其他思想系统在整体上作出否定性的评价。换言之,不同于在儒家经典诠释传统中,后起的学者为了谋求自身思想观念的合法性而采取“以述为作”的方式以充分突显其思想系统与前此相关思想系统的继承性,在西方诠释传统中,后起的思想系统恰恰是要通过指证前此相关思想系统的局限性来反显自身的革命性,以为自己确立存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儒家经典诠释传统中后起思想系统与此前思想系统之间的关系比喻为一波一波紧紧相连的波浪,而西方诠释传统中后起思想系统与此前思想系统之间的关系则可以看作一座座突兀而起的山峰。黑格尔对西方哲学史演进历程的描述,可以看作是十分典型地状述了西方诠释传统的这一理论特质。黑格尔把哲学史比喻为一个“厮杀的战场”:“全部哲学史就这样成了一个战场,堆满着死人的骨骼。它是一个死人的王国,这王国不仅充满着肉体死亡了的个人,而且充满着已经推翻了的和精神上死亡了的系统,在这里面,每一个杀死了另一个,并且埋葬了另一个”。“这样的情形当然就发生了:一种新的哲学出现了。这哲学断言所有别的哲学都是毫无价值的。诚然,每一个哲学出现时,都自诩为:有了它,前此的一切哲学不仅是被驳倒了,而且它们的缺点也被补救了,正确的哲学最后被发现了。但根据以前的许多经验,倒足以表明新约里的另一些话同样地可以用来说这样的哲学,----使徒彼德对安那尼亚说:‘看吧!将要抬你出去的人的脚,已经站在门口。’且看那要驳倒你并且代替你的哲学也不会很久不来,正如它对于其他的哲学也并不会很久下去一样。”[2]
如果承认在儒家经典诠释传统中存在着上述理论特质,可以进一步讨论的是:出现上述理论特质的原因何在?接下来本文就从一个侧面对此试作进一步探讨。关于这个话题同样可以从孔子说起。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感谢每一位辛勤著写的作者,感谢每一位的分享。

相关资料

- 有价值
- 一般般
- 没价值








24小时热门
推荐阅读
关于我们

APP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