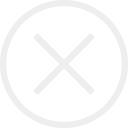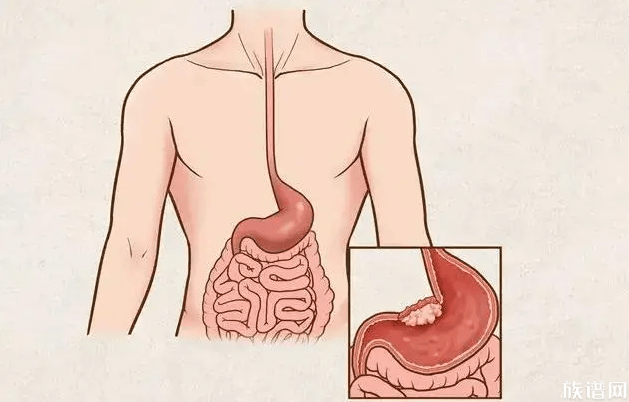微州文化—微州印象—徽州女人
微州文化—微州印象—徽州女人,耍猴的徽州人眼睛像冰块一样寒冷而晶莹,他的刀把子般的长脸呈现出灰暗的菜色,微微仰
耍猴的徽州人眼睛像冰块一样寒冷而晶莹,他的刀把子般的长脸呈现出灰暗的菜色,微
微仰着,看小站候车室顶上的水泥字块。他看见龙家湾三个字都是向后倒下去的,旁边加固
的铁丝被风吹得飒飒地响。秋风凉了,徽州人在站台上打了个寒噤。看来他是沿着铁路流浪
到这里的,从皖南走过来不知要走多长时间。徽州人挑着担子,一只箩筐里是棉被和干粮,
另一只箩筐里装的他的小棕猴。引人注目的就是那只猴子,它的毛茸茸的脖颈处套着一个银
项圈,闪出圆圆的光晕来。猴子的模样有点怪,额际上长着一撮白毛,像黑土地里的孤独的
雪堆。候车室里有河南女人把头探出窗外,朝月台上张望,她们看见那个徽州人把猴子抱在
腿上,正在给它穿一条花布小褂。猴子很安静,猴子的花布小褂已经脏得不能再脏了。猴子
在徽州人怀里猛地一窜,女人便咦咦呀呀地叫起来,一边就涌出了候车室的玻璃门。 “耍呀,耍呀,耍起来呀。”很快有一群人把徽州人和他的猴子围起来了。徽州人抬起
头,有点惊慌地扫视着四周的人群。他的干菜色的刀把子脸上浮出一个谦恭的微笑,还是像
冰块一样,寒冷而晶莹的。他一只手拽着猴子颈上的银项圈,另一只手伸到棉袄里去,迟迟
疑疑地掏,慢慢掏出一面小铜锣来。“耍呀,耍呀,俺们给你钱。”那几个去南方贩棉花的
河南女人朗朗地喊。笑着摊搡着从人群外面挤到前面。徽州人不动弹地坐在月台上。小铜锣
的光面映出他的枯槁的倦容,他的眼神中有一片浑浑沌沌的雾气弥满了水泥月台,使围观的
人们感到了陌生的凉意。 咣——徽州人终于果断地敲响了小铜锣,把怀里的小棕猴颠了出去。猴子在空中翻了个
筋斗,肮脏的花布小褂飘了飘,站到地上,不动了。猴子的猩红色的瞳仁很怪异地亮着,射
到每个人的脸上。“耍呀,这猴子怎么不动了?”从河南来的女人们往后退了几步,有些惶
惑。她们发现徽州人的猴子跟以前常见的不一样。猴眼里有类似人的目光闪闪烁烁的。 月台上突然沉寂了一刻。徽州人直愣愣地瞪着他的猴子,又砸了一下小铜锣。猴子仍然
像个小人一样,保持它的站立姿势。徽州人喉咙里痛苦地咕噜一声,望了望龙家湾的天空。
然后他朝那只顽固的猴子挪过去,猛地揪住了猴子脖颈上套着的银项圈,一下一下地蹬着。 “你给我翻!你给我跳!”徽州人低沉的声音透出杀性。小棕猴被银项圈勒得吱吱乱
叫,拼命挣扎着,即使是此刻它眼睛里的红光仍然在不停闪烁,只是头仰起来,艰难地射到
了主人那张渐渐暴虐的脸上。 “哎哟,这猴子!”湖南女人们突然嚷起来,她们看见那只猴子在挣扎中突然窜起来,
前爪在徽州人脸上狠狠地扑打了一下。所有人都见到了这奇怪的一幕。徽州人用手捂住了
脸,但殷红的血还是从他糙黄的指出来了。好像这是他预料中的,徽州人一声不吭,在
众人的一片唏嘘惊叹声中,他又一次仰起脸,注视着龙家湾车站上空寂寥的天际。他脸上那
道血印很深也很长,像一支箭矢的形状射出去。龙家湾的天空这时候已经变成灰朦朦的了。
棉絮般的云团藏匿得无影无踪,从远山口吹来的风挟着阴冷而潮湿的气息,雨快落下来了。
“这家伙,他根本就不会耍猴的。”河南女人们窃窃私语,但她们还是慷慨地打开了花花绿
绿的荷包,把纸币用石子压在月台上,徽州人的脚下,然后她们就背着硕大的棉花包去等车
了。过了会远远地看那纸币,仍躺在石子底下。傍晚那辆车马上要驶进龙家湾小站了,天要
下雨了。是一片河水干涸后形成的洼地,夏天的时候长满了金黄色花盘的向日葵,让南来北
往的外乡人觉得龙家湾小站是金黄色的小岛,朝着铁道放出那种浅浅的芬芳。还有水潭,深
藏在绿杆子黄花盘下,闪着玻璃的光芒。 哑佬卧在一堆枕木上养精气时,发现洼地里有片葵花杆子潮水似的涌动,浮出一个红影
子。原来是个女人,正从路坡下面爬上来。哑佬直愣愣地瞧那女人钻出了葵花地。她背上压
着一个鼓鼓的包裹卷,越过铁道时她抬手掠了下被风弄乱的头发。女人朝他走过来,笑着,
哑佬从没看见过女人这样白得像玉石的牙齿。“大哥,你们这儿,”女人顿了顿,迟疑地
问:“见到一个耍猴人过去吗?”这年有八个耍猴人走过龙家湾了,哑佬算计着。但他不知
道女人说的是哪一个。哑佬对她咧嘴一笑,很鄙视地捏捏自己的嘴,然后含含糊糊地吐出一
个字: “不。”哑佬讲不出完整的语言,但是学会了说这个“不”字。不知道女人懂没懂哑佬
的意思。她站在月台下面的某片阴影中,朝铁道两侧四处张望。暮色渐渐浓重,漾开了覆盖
住洼地里的向日葵林,那些黑压压的茎杆乱挤着,发出一阵轻微的倒伏声。“这地方葵花儿
真多呀。”女人自言自语。“不。”哑佬想说夏天才是葵花世界,那会儿龙家湾的人眼睛里
全是金黄色的的花盘摇啊摇的。女人侧过脸注意了哑佬的神情,恍然地又一笑,哑佬忽然想
到有的女人就像一株夏天的向日葵,美丽而蛊惑人心。 哑佬就把陌生女人往老锛子的办公室里带。老锛子是龙家湾的站长。他一天到晚在房子
里描描划划打电话接电话的,但是老锛子关照过,站上来了什么古怪的人得带到他的办公室
里来,站在门边上就行了,不准走到他身边去。于是那个女人就倚着门,从哑佬宽阔的肩背
后打量着老锛子的办公室。老锛子的斜眼从老光镜片后深沉地测量着女人的行踪。“从南面
来的?”“从南面搭火车来的。” “怎么又不搭火车了?” “没钱啦,半路上给撵下来的。” “你一个女人跑出来东浪西颠的干什么?”“我找我男人呐。大哥,你看见一个耍猴的
过这儿吗?”“咦,你这么个漂亮女人连耍猴的都拴不住还能干什么?”老锛子瘪起嘴摇着
头,从耳朵上挟起一支圆珠笔,端正地在什么纸上一连画了好几个圈圈。老锛子花白头发的
脑壳转也不转了。办公室的四壁都有葵花杆子黯淡地立着。“你回家乡吧,耍猴人走遍四
方,上哪儿去找?”“我不回。他把我当姑娘时的银项圈当猴套呢,他死了我才不管,那猴
子死不了,银项圈也烂不掉,追到天边我要把银项圈追回来。”女人倚着门,水亮的短发髻
焦躁地磨擦着原木门框,背上的花花绿绿的包裹卷碰到了一捆葵花杆子,葵花杆子就沙沙鸣
响着倒在女人的脚边。 老锛子回过头隐晦地朝陌生女人笑,笑了一会又瘪起嘴说:“你留在这儿等着他回来
吧,耍猴人不认路,都沿着铁路走,都要走过龙家湾的。”“那死鬼不会回来了,他把我的
银项圈都带走了。”“留在这儿吧,马上龙家湾就下来葵花籽了,等瓜子嗑完了,你家耍猴
的也回来了。” “你这老家伙真是的,我干嘛要听你的留下来嗑瓜子呢?”“留下来吧,给站上干点活
攒点钱再回家。”女人梳得一丝不苟的发髻低垂下去,突然显出了柔弱的模样,她朝哑佬望
了望,哑佬的脸上充满了笨拙的。她转过脸去看墙边四角里的葵花杆子,葵花杆子都歪
斜地站着,发散出夏天的气息。“我走不动了,就在这里等他吧。”女人叹息了一声。老锛
子和哑佬看见陌生女人一下子就瘫软地坐下去了。她很累。她一低头哑佬就看见那团发髻里
插着一支奇怪的头簪,那头簪像一把小刀的形状,锥顶闪着一点冷光。每天一早一晚,龙家
湾有黑龙般的货车靠站。戴鸭舌帽的司机发现了这小站产生的些微的变化,矮房前的晾衣绳
上竟飘开了花花绿绿的女人衣物,空气中也因而夹杂着一丝讨人喜爱的温情的气味。“哑
佬,你娶老婆了吗?”司机们朝扛货包的人群嚷。“不。”哑佬极艰难地吐出一句,眼睛却
快乐而多情地转动着,去寻找女人银月。银月远远地闪现在秋天的向日葵林里,在哑佬的视
线里,穿黄衫子的银月就像一株向日葵沿着路坡滑动,画出一些黄灿灿的图案,把他的眼都
晃迷糊了。银月在割草,秋天的草都干黄了,银月就割满坡上干黄的草。她给龙家湾的男人
们蒸好吃一天的馒头就下坡了。银月割了那么多草,全都懒懒地码在月台上,干黄干黄的,
码成一座座憔悴的小山包。哑佬卸完车就常常光着膀子在那些干草堆里绕来绕去,变化着走
出各种路线,对这套动作有着孩童的痴迷。“哑佬,你在找什么?”老锛子花白的脑袋探出
窗户。“不。”哑佬像蛇一样贴着草堆游,游出一个波浪形。“在找女人么?混蛋哑佬!”
老锛子对哑佬狠狠地唾了一口。看看那些草垛,越来越多,越来越高,要把月台盖满了,老
锛子说:“银月割那么多草干什么?真他妈会瞎搞,站台上怎么能晒草呢?又不是在她们的
庄子里。” 哑佬站住不动了。他听见远远地从向日葵林里飘过来银月唱的徽州小调,沙哑而伤心
的。他眼睛却分明被草垛里的某一片光亮吸住了,哑佬的两只手鲁莽地去捅那片光亮,干草
垛微微倾颓了,叮一声,什么东西掉在哑佬的脚下。是一支头簪,银亮亮的,仿佛古怪的小
刀儿闪着光,照亮呆立的哑佬。哑佬捡起银簪吹了吹,没有灰尘,却吹出一股类似向日葵的
淡淡的香味。哑佬朝路坡那里张望,银月的黄衫子已经滑落到坡底,在一片葵花杆子和干草
丛中间一点点地闪烁。银月你这个怪女人,割这么多草干什么用呢? 后来哑佬把那支银簪藏在宽宽的裤腰带里,他粗粗地喘着气,又闭上眼睛。眼里便湿热
得很,全是夏天的向日葵作着温情的燃烧。银月,银月,你割这么多草干什么用呢?“站
长,我的簪子丢了。”女人脸色煞白地站在老锛子的办公桌前,身上的衣服被汗泡湿了,裹
紧了。女人浑身都落了星星点点的草棵子。 “簪子丢了?”老锛子在表格上画着他熟稔的圆圈儿,说:“掉在葵花地里了吧?谁让
你鬼迷心窍样地割草,割,割,这下好,把簪子给割丢了。” “丢了。我漫坡都找过了,没有我的银簪子。”“真丢了?再找找吧,龙家湾丢不了东
西。”“我活不下去了。那簪子和银项圈是成天地的,项圈让那死鬼偷跑了,簪子怎么又不
见了——天老爷,我活不下去了。”女人紧紧咬住的发紫的嘴唇猛地启开,冲出一声悲痛欲
绝的哽咽,那声音像石头碎裂一样发散出蛮力,办公室四壁的葵花杆子莫名地震颤起来。老
锛子坐不住了。“银月,别急,说不定簪子让谁捡到了呢?”“我出来追银项圈的,怎么想
到簪子也会没了呢?那簪子和银项圈是成天地的,一只都不能缺呀。天老爷,我活不下去
啦!”女人的哭声渐渐流利了,舒畅了,渐渐又像母兽一样低沉地呻吟着。女人的眼里充满
绝望,灰黑一片压得老锛子的办公室也喘不过气来。老锛子抱住花白的脑袋摇晃了一会,用
棉花团擦着镜片,女人在镜片里缩成一团地哭。“你这女人哟,你这样可真是活不下去
了。”窗外正过了溜铁皮车,铁轨铮铮地响了半天,车头冒出来的黑烟灌进老锛子的办公
室,老锛子便用手去扑打那蔓延的黑烟,等黑烟散尽,银月已经不见了。老锛子赶到门口,
看见银月在月台上追着那溜铁皮车,黄衫子被车轮下面的劲风吹着,鼓荡起来,如同野蛱蝶
嘤嘤地要起飞的样子。“银月,你干什么?”老锛子在狂吼起来。“耍猴的,有耍猴的—
—”银月的声音被火车声卷过去。“银月,你回来啊别追车啊——”老锛子去抓红信号旗
了。“车上有耍猴的——”银月的声音又被火车声卷过来。老锛子明白了什么。他猜银月跑
累了就会回来的。老锛子在他的办公室里站了会,把墙角上总是莫名其妙倒下的葵花杆子扶
起来。他又想起银月的事,这世界这么野蛮旷大,银月的头簪和项圈到底在哪里呢? 晚上下了秋露,银月沿着铁道走回来时,人影儿带着一层朦胧的水色。浓重的露水将这
个女人画在龙家湾小站的月台上,画成一株硕大的向日葵。 “你看见你男人啦?”老锛子举起巡路灯照亮了银月。“我看见了,清清楚楚的一个耍
猴人,还有我的银项圈,挂在猴子的颈上,我追上去怎么就不见了呢,要不就是我没追
上?”“不一定是你男人,这铁路边过的耍猴人多着呢。”银月的脸在昏黄的灯光里现出了
半边轮廓,老锛子便觉得这个女人有一半枯槁憔悴,另一半却惊人的美丽了。那几天里,龙
家湾人都疯了似地散在长长的铁路路坡上,乱七八糟地寻找一个女人丢失的银簪子。男人们
的大脚丫子踩倒了大片大片的葵花杆子,不少的葵花叶葵花杆碎裂了,咔喳喳痛苦地响起
来。哑佬躲在银月割下的草垛子后面,狡狯而得意地张大嘴,俯瞰路坡下面忙忙碌碌的人
影。哑佬知道他们找不到那支银簪子。银簪子是有光亮的。他们找死了也见不着那点光亮,
路坡下只有黑乎乎的粘土,黑乎乎的秋后的向日葵。没有银月的簪子。“哑佬,你捡到一支
银簪子了吗?”老锛子多次虎着脸逼问哑佬,企图从那双野兽般迷茫的眼睛里找到什么。
“不。”哑佬仰着头说。他的两只手坚实地护着肮脏的散出汗腥气的腰带,轻轻地摩挲着。 银月走过哑佬身边时没有这样问过,她相信哑佬是个老实人,捡了她的银簪子不会不还
她。银月见了哑佬总是要笑,哑佬就觉得那女人的银簪子正以小刀似的顶口一下一下地捅着
他,他按住腰带下的簪子,还是觉得疼。哑佬不要这女人对他露出玉石样的牙齿,笑。 “不,不。”哑佬这样拼命地喊,但发出的声音却极小极沉闷。失魂落魄的女人听不懂
哑佬的话。 一天清晨,龙家湾人发现那个从南面来的女人了。留下好多干草垛孤零零地站在月
台上。风很大,掀起一缕缕干草漫天飞舞,站上的人们不知怀了一种什么心情,都冒着风聚
过来看风中的干草堆。风不停地挟走枯黄的轻飘飘的干草,清冽的空气中满是细小的尘土和
干草根腐烂的味道。老锛子披了大衣出办公室,望着随风飞扬的干草,那张老头的脸上浮现
出人世的苍茫:“银月那女人又去追耍猴的啦。可是她的银簪子掉在我们龙家湾呢,现在她
身上什么都没了。” 那天的风劲少有,刮得小站房顶上的龙家湾三个字也像向日葵林一样倒伏下来。人们的
头上身上落满了细草棵子,却都朝灰蒙蒙的铁路尽头望,铁路尽头就是灰蒙蒙的什么也没
有。银月那女人已经走远了。 有人发现洼地里传来一阵古怪的声音,循声望去,那里的葵花杆子全都伏倒了,唯有一
处还硬硬地挺着,一个人呆傻地抱着那处葵花杆子在哭,是卸货的哑佬。哑佬死于次年夏
天,是龙家湾向日葵开得最闹的时辰。哑佬死得怪,他卸完货跳到池塘里洗了澡,洗完澡就
一直躺在葵花地里,后来老锛子带人找到他,看见他的胸口上插着一支银簪子,那银簪子的
样子本身就像一把锋利的小刀。翻开哑佬的冰凉的眼皮,瞳仁里装满了金灿灿大朵大朵的向
日葵花。哑佬死得很蹊跷,一般来说一支银簪子是不能置人于死地的。后来龙家湾的站长老
锛了收藏了那支银簪。每年收瓜子的季节,他都注意着走过铁道的那些外乡人,但是给人印
象很深的徽州女人银月却没再经过龙家湾,或者她经过这里却没有看见。老锛子这两年更显
老了,但是他跟人提起这故事时,总还是神色怅惘地叹道:“她的银簪子在我这里,她的银
项圈谁知道在哪里呢?”哑佬的新坟立在向日葵地里,龙家湾小站的人从来没有怀疑这徽州
女人和哑佬之死有什么关系。
微仰着,看小站候车室顶上的水泥字块。他看见龙家湾三个字都是向后倒下去的,旁边加固
的铁丝被风吹得飒飒地响。秋风凉了,徽州人在站台上打了个寒噤。看来他是沿着铁路流浪
到这里的,从皖南走过来不知要走多长时间。徽州人挑着担子,一只箩筐里是棉被和干粮,
另一只箩筐里装的他的小棕猴。引人注目的就是那只猴子,它的毛茸茸的脖颈处套着一个银
项圈,闪出圆圆的光晕来。猴子的模样有点怪,额际上长着一撮白毛,像黑土地里的孤独的
雪堆。候车室里有河南女人把头探出窗外,朝月台上张望,她们看见那个徽州人把猴子抱在
腿上,正在给它穿一条花布小褂。猴子很安静,猴子的花布小褂已经脏得不能再脏了。猴子
在徽州人怀里猛地一窜,女人便咦咦呀呀地叫起来,一边就涌出了候车室的玻璃门。 “耍呀,耍呀,耍起来呀。”很快有一群人把徽州人和他的猴子围起来了。徽州人抬起
头,有点惊慌地扫视着四周的人群。他的干菜色的刀把子脸上浮出一个谦恭的微笑,还是像
冰块一样,寒冷而晶莹的。他一只手拽着猴子颈上的银项圈,另一只手伸到棉袄里去,迟迟
疑疑地掏,慢慢掏出一面小铜锣来。“耍呀,耍呀,俺们给你钱。”那几个去南方贩棉花的
河南女人朗朗地喊。笑着摊搡着从人群外面挤到前面。徽州人不动弹地坐在月台上。小铜锣
的光面映出他的枯槁的倦容,他的眼神中有一片浑浑沌沌的雾气弥满了水泥月台,使围观的
人们感到了陌生的凉意。 咣——徽州人终于果断地敲响了小铜锣,把怀里的小棕猴颠了出去。猴子在空中翻了个
筋斗,肮脏的花布小褂飘了飘,站到地上,不动了。猴子的猩红色的瞳仁很怪异地亮着,射
到每个人的脸上。“耍呀,这猴子怎么不动了?”从河南来的女人们往后退了几步,有些惶
惑。她们发现徽州人的猴子跟以前常见的不一样。猴眼里有类似人的目光闪闪烁烁的。 月台上突然沉寂了一刻。徽州人直愣愣地瞪着他的猴子,又砸了一下小铜锣。猴子仍然
像个小人一样,保持它的站立姿势。徽州人喉咙里痛苦地咕噜一声,望了望龙家湾的天空。
然后他朝那只顽固的猴子挪过去,猛地揪住了猴子脖颈上套着的银项圈,一下一下地蹬着。 “你给我翻!你给我跳!”徽州人低沉的声音透出杀性。小棕猴被银项圈勒得吱吱乱
叫,拼命挣扎着,即使是此刻它眼睛里的红光仍然在不停闪烁,只是头仰起来,艰难地射到
了主人那张渐渐暴虐的脸上。 “哎哟,这猴子!”湖南女人们突然嚷起来,她们看见那只猴子在挣扎中突然窜起来,
前爪在徽州人脸上狠狠地扑打了一下。所有人都见到了这奇怪的一幕。徽州人用手捂住了
脸,但殷红的血还是从他糙黄的指出来了。好像这是他预料中的,徽州人一声不吭,在
众人的一片唏嘘惊叹声中,他又一次仰起脸,注视着龙家湾车站上空寂寥的天际。他脸上那
道血印很深也很长,像一支箭矢的形状射出去。龙家湾的天空这时候已经变成灰朦朦的了。
棉絮般的云团藏匿得无影无踪,从远山口吹来的风挟着阴冷而潮湿的气息,雨快落下来了。
“这家伙,他根本就不会耍猴的。”河南女人们窃窃私语,但她们还是慷慨地打开了花花绿
绿的荷包,把纸币用石子压在月台上,徽州人的脚下,然后她们就背着硕大的棉花包去等车
了。过了会远远地看那纸币,仍躺在石子底下。傍晚那辆车马上要驶进龙家湾小站了,天要
下雨了。是一片河水干涸后形成的洼地,夏天的时候长满了金黄色花盘的向日葵,让南来北
往的外乡人觉得龙家湾小站是金黄色的小岛,朝着铁道放出那种浅浅的芬芳。还有水潭,深
藏在绿杆子黄花盘下,闪着玻璃的光芒。 哑佬卧在一堆枕木上养精气时,发现洼地里有片葵花杆子潮水似的涌动,浮出一个红影
子。原来是个女人,正从路坡下面爬上来。哑佬直愣愣地瞧那女人钻出了葵花地。她背上压
着一个鼓鼓的包裹卷,越过铁道时她抬手掠了下被风弄乱的头发。女人朝他走过来,笑着,
哑佬从没看见过女人这样白得像玉石的牙齿。“大哥,你们这儿,”女人顿了顿,迟疑地
问:“见到一个耍猴人过去吗?”这年有八个耍猴人走过龙家湾了,哑佬算计着。但他不知
道女人说的是哪一个。哑佬对她咧嘴一笑,很鄙视地捏捏自己的嘴,然后含含糊糊地吐出一
个字: “不。”哑佬讲不出完整的语言,但是学会了说这个“不”字。不知道女人懂没懂哑佬
的意思。她站在月台下面的某片阴影中,朝铁道两侧四处张望。暮色渐渐浓重,漾开了覆盖
住洼地里的向日葵林,那些黑压压的茎杆乱挤着,发出一阵轻微的倒伏声。“这地方葵花儿
真多呀。”女人自言自语。“不。”哑佬想说夏天才是葵花世界,那会儿龙家湾的人眼睛里
全是金黄色的的花盘摇啊摇的。女人侧过脸注意了哑佬的神情,恍然地又一笑,哑佬忽然想
到有的女人就像一株夏天的向日葵,美丽而蛊惑人心。 哑佬就把陌生女人往老锛子的办公室里带。老锛子是龙家湾的站长。他一天到晚在房子
里描描划划打电话接电话的,但是老锛子关照过,站上来了什么古怪的人得带到他的办公室
里来,站在门边上就行了,不准走到他身边去。于是那个女人就倚着门,从哑佬宽阔的肩背
后打量着老锛子的办公室。老锛子的斜眼从老光镜片后深沉地测量着女人的行踪。“从南面
来的?”“从南面搭火车来的。” “怎么又不搭火车了?” “没钱啦,半路上给撵下来的。” “你一个女人跑出来东浪西颠的干什么?”“我找我男人呐。大哥,你看见一个耍猴的
过这儿吗?”“咦,你这么个漂亮女人连耍猴的都拴不住还能干什么?”老锛子瘪起嘴摇着
头,从耳朵上挟起一支圆珠笔,端正地在什么纸上一连画了好几个圈圈。老锛子花白头发的
脑壳转也不转了。办公室的四壁都有葵花杆子黯淡地立着。“你回家乡吧,耍猴人走遍四
方,上哪儿去找?”“我不回。他把我当姑娘时的银项圈当猴套呢,他死了我才不管,那猴
子死不了,银项圈也烂不掉,追到天边我要把银项圈追回来。”女人倚着门,水亮的短发髻
焦躁地磨擦着原木门框,背上的花花绿绿的包裹卷碰到了一捆葵花杆子,葵花杆子就沙沙鸣
响着倒在女人的脚边。 老锛子回过头隐晦地朝陌生女人笑,笑了一会又瘪起嘴说:“你留在这儿等着他回来
吧,耍猴人不认路,都沿着铁路走,都要走过龙家湾的。”“那死鬼不会回来了,他把我的
银项圈都带走了。”“留在这儿吧,马上龙家湾就下来葵花籽了,等瓜子嗑完了,你家耍猴
的也回来了。” “你这老家伙真是的,我干嘛要听你的留下来嗑瓜子呢?”“留下来吧,给站上干点活
攒点钱再回家。”女人梳得一丝不苟的发髻低垂下去,突然显出了柔弱的模样,她朝哑佬望
了望,哑佬的脸上充满了笨拙的。她转过脸去看墙边四角里的葵花杆子,葵花杆子都歪
斜地站着,发散出夏天的气息。“我走不动了,就在这里等他吧。”女人叹息了一声。老锛
子和哑佬看见陌生女人一下子就瘫软地坐下去了。她很累。她一低头哑佬就看见那团发髻里
插着一支奇怪的头簪,那头簪像一把小刀的形状,锥顶闪着一点冷光。每天一早一晚,龙家
湾有黑龙般的货车靠站。戴鸭舌帽的司机发现了这小站产生的些微的变化,矮房前的晾衣绳
上竟飘开了花花绿绿的女人衣物,空气中也因而夹杂着一丝讨人喜爱的温情的气味。“哑
佬,你娶老婆了吗?”司机们朝扛货包的人群嚷。“不。”哑佬极艰难地吐出一句,眼睛却
快乐而多情地转动着,去寻找女人银月。银月远远地闪现在秋天的向日葵林里,在哑佬的视
线里,穿黄衫子的银月就像一株向日葵沿着路坡滑动,画出一些黄灿灿的图案,把他的眼都
晃迷糊了。银月在割草,秋天的草都干黄了,银月就割满坡上干黄的草。她给龙家湾的男人
们蒸好吃一天的馒头就下坡了。银月割了那么多草,全都懒懒地码在月台上,干黄干黄的,
码成一座座憔悴的小山包。哑佬卸完车就常常光着膀子在那些干草堆里绕来绕去,变化着走
出各种路线,对这套动作有着孩童的痴迷。“哑佬,你在找什么?”老锛子花白的脑袋探出
窗户。“不。”哑佬像蛇一样贴着草堆游,游出一个波浪形。“在找女人么?混蛋哑佬!”
老锛子对哑佬狠狠地唾了一口。看看那些草垛,越来越多,越来越高,要把月台盖满了,老
锛子说:“银月割那么多草干什么?真他妈会瞎搞,站台上怎么能晒草呢?又不是在她们的
庄子里。” 哑佬站住不动了。他听见远远地从向日葵林里飘过来银月唱的徽州小调,沙哑而伤心
的。他眼睛却分明被草垛里的某一片光亮吸住了,哑佬的两只手鲁莽地去捅那片光亮,干草
垛微微倾颓了,叮一声,什么东西掉在哑佬的脚下。是一支头簪,银亮亮的,仿佛古怪的小
刀儿闪着光,照亮呆立的哑佬。哑佬捡起银簪吹了吹,没有灰尘,却吹出一股类似向日葵的
淡淡的香味。哑佬朝路坡那里张望,银月的黄衫子已经滑落到坡底,在一片葵花杆子和干草
丛中间一点点地闪烁。银月你这个怪女人,割这么多草干什么用呢? 后来哑佬把那支银簪藏在宽宽的裤腰带里,他粗粗地喘着气,又闭上眼睛。眼里便湿热
得很,全是夏天的向日葵作着温情的燃烧。银月,银月,你割这么多草干什么用呢?“站
长,我的簪子丢了。”女人脸色煞白地站在老锛子的办公桌前,身上的衣服被汗泡湿了,裹
紧了。女人浑身都落了星星点点的草棵子。 “簪子丢了?”老锛子在表格上画着他熟稔的圆圈儿,说:“掉在葵花地里了吧?谁让
你鬼迷心窍样地割草,割,割,这下好,把簪子给割丢了。” “丢了。我漫坡都找过了,没有我的银簪子。”“真丢了?再找找吧,龙家湾丢不了东
西。”“我活不下去了。那簪子和银项圈是成天地的,项圈让那死鬼偷跑了,簪子怎么又不
见了——天老爷,我活不下去了。”女人紧紧咬住的发紫的嘴唇猛地启开,冲出一声悲痛欲
绝的哽咽,那声音像石头碎裂一样发散出蛮力,办公室四壁的葵花杆子莫名地震颤起来。老
锛子坐不住了。“银月,别急,说不定簪子让谁捡到了呢?”“我出来追银项圈的,怎么想
到簪子也会没了呢?那簪子和银项圈是成天地的,一只都不能缺呀。天老爷,我活不下去
啦!”女人的哭声渐渐流利了,舒畅了,渐渐又像母兽一样低沉地呻吟着。女人的眼里充满
绝望,灰黑一片压得老锛子的办公室也喘不过气来。老锛子抱住花白的脑袋摇晃了一会,用
棉花团擦着镜片,女人在镜片里缩成一团地哭。“你这女人哟,你这样可真是活不下去
了。”窗外正过了溜铁皮车,铁轨铮铮地响了半天,车头冒出来的黑烟灌进老锛子的办公
室,老锛子便用手去扑打那蔓延的黑烟,等黑烟散尽,银月已经不见了。老锛子赶到门口,
看见银月在月台上追着那溜铁皮车,黄衫子被车轮下面的劲风吹着,鼓荡起来,如同野蛱蝶
嘤嘤地要起飞的样子。“银月,你干什么?”老锛子在狂吼起来。“耍猴的,有耍猴的—
—”银月的声音被火车声卷过去。“银月,你回来啊别追车啊——”老锛子去抓红信号旗
了。“车上有耍猴的——”银月的声音又被火车声卷过来。老锛子明白了什么。他猜银月跑
累了就会回来的。老锛子在他的办公室里站了会,把墙角上总是莫名其妙倒下的葵花杆子扶
起来。他又想起银月的事,这世界这么野蛮旷大,银月的头簪和项圈到底在哪里呢? 晚上下了秋露,银月沿着铁道走回来时,人影儿带着一层朦胧的水色。浓重的露水将这
个女人画在龙家湾小站的月台上,画成一株硕大的向日葵。 “你看见你男人啦?”老锛子举起巡路灯照亮了银月。“我看见了,清清楚楚的一个耍
猴人,还有我的银项圈,挂在猴子的颈上,我追上去怎么就不见了呢,要不就是我没追
上?”“不一定是你男人,这铁路边过的耍猴人多着呢。”银月的脸在昏黄的灯光里现出了
半边轮廓,老锛子便觉得这个女人有一半枯槁憔悴,另一半却惊人的美丽了。那几天里,龙
家湾人都疯了似地散在长长的铁路路坡上,乱七八糟地寻找一个女人丢失的银簪子。男人们
的大脚丫子踩倒了大片大片的葵花杆子,不少的葵花叶葵花杆碎裂了,咔喳喳痛苦地响起
来。哑佬躲在银月割下的草垛子后面,狡狯而得意地张大嘴,俯瞰路坡下面忙忙碌碌的人
影。哑佬知道他们找不到那支银簪子。银簪子是有光亮的。他们找死了也见不着那点光亮,
路坡下只有黑乎乎的粘土,黑乎乎的秋后的向日葵。没有银月的簪子。“哑佬,你捡到一支
银簪子了吗?”老锛子多次虎着脸逼问哑佬,企图从那双野兽般迷茫的眼睛里找到什么。
“不。”哑佬仰着头说。他的两只手坚实地护着肮脏的散出汗腥气的腰带,轻轻地摩挲着。 银月走过哑佬身边时没有这样问过,她相信哑佬是个老实人,捡了她的银簪子不会不还
她。银月见了哑佬总是要笑,哑佬就觉得那女人的银簪子正以小刀似的顶口一下一下地捅着
他,他按住腰带下的簪子,还是觉得疼。哑佬不要这女人对他露出玉石样的牙齿,笑。 “不,不。”哑佬这样拼命地喊,但发出的声音却极小极沉闷。失魂落魄的女人听不懂
哑佬的话。 一天清晨,龙家湾人发现那个从南面来的女人了。留下好多干草垛孤零零地站在月
台上。风很大,掀起一缕缕干草漫天飞舞,站上的人们不知怀了一种什么心情,都冒着风聚
过来看风中的干草堆。风不停地挟走枯黄的轻飘飘的干草,清冽的空气中满是细小的尘土和
干草根腐烂的味道。老锛子披了大衣出办公室,望着随风飞扬的干草,那张老头的脸上浮现
出人世的苍茫:“银月那女人又去追耍猴的啦。可是她的银簪子掉在我们龙家湾呢,现在她
身上什么都没了。” 那天的风劲少有,刮得小站房顶上的龙家湾三个字也像向日葵林一样倒伏下来。人们的
头上身上落满了细草棵子,却都朝灰蒙蒙的铁路尽头望,铁路尽头就是灰蒙蒙的什么也没
有。银月那女人已经走远了。 有人发现洼地里传来一阵古怪的声音,循声望去,那里的葵花杆子全都伏倒了,唯有一
处还硬硬地挺着,一个人呆傻地抱着那处葵花杆子在哭,是卸货的哑佬。哑佬死于次年夏
天,是龙家湾向日葵开得最闹的时辰。哑佬死得怪,他卸完货跳到池塘里洗了澡,洗完澡就
一直躺在葵花地里,后来老锛子带人找到他,看见他的胸口上插着一支银簪子,那银簪子的
样子本身就像一把锋利的小刀。翻开哑佬的冰凉的眼皮,瞳仁里装满了金灿灿大朵大朵的向
日葵花。哑佬死得很蹊跷,一般来说一支银簪子是不能置人于死地的。后来龙家湾的站长老
锛了收藏了那支银簪。每年收瓜子的季节,他都注意着走过铁道的那些外乡人,但是给人印
象很深的徽州女人银月却没再经过龙家湾,或者她经过这里却没有看见。老锛子这两年更显
老了,但是他跟人提起这故事时,总还是神色怅惘地叹道:“她的银簪子在我这里,她的银
项圈谁知道在哪里呢?”哑佬的新坟立在向日葵地里,龙家湾小站的人从来没有怀疑这徽州
女人和哑佬之死有什么关系。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感谢每一位辛勤著写的作者,感谢每一位的分享。
——— 没有了 ———
编辑:阿族小谱

相关资料

文章价值打分
- 有价值
- 一般般
- 没价值
当前文章打 0 分,共有 0 人打分
文章观点支持

0

0
文章很值,打赏犒劳一下作者~

打赏
私信
24小时热门
推荐阅读
· 微州文化—微州印象—徽州唐模村
徽州唐模村游记“徽州”,这个似乎带着历史沧桑味道和乡土气息的字眼,很久很久以前就在我的心灵中跃动,梦幻中理理模糊的思路脉络,探其究,主要缘于那里独有的那种正在淡去的古老文明的余味,有着现今保存完好的传统民间文化,有着千百年来“徽州”人不断营造的独特乡土,有着一种让后人受用至今的生存理念……。而“徽州”的唐模村就是其中的典范。“徽州”的唐模村地处安徽的南部,为歙县所辖。传说中是唐朝中国农村的文明模范村。村中以水街、古树、古桥等人文自然景观闻名于世。去过徽州唐模村旅游,无不被古徽水街上那恬淡自得的人们,被那“枯塍、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风景所吸引。终于有了一天,深秋时节,几个驴友、色友共同商议,AA制,去探访一下这千百年来蕴育着神奇色彩的古村落。从浙江到歙县约800里程,我们赶忙驱车前往,定下GPS线路,大家轮流驾驶,一路奔波,好是辛苦,约八个小时的时间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个让人牵魂挂肚的...
· 微州文化—微州印象—从守活寡的徽州女人说起
一部叫"徽州女人"的戏前段时间在上海演,并博得上海传媒的好评.据介绍,情节是这样的:一少女出嫁,而丈夫逃婚,35年后,逃婚的男人带着妻子孩子归来,这个前少女平静的接受了,并自称是孩子的姑姑.在接受"文汇报"采访时,编剧陈薪伊说,封建糟粕是十分粗浅的提法,我想在剧中表现徽文化的深厚底蕴和人格魅力.这部戏的徽州女人就是我母亲,在我们皖南,许多女人都是这样.而主演韩再芬说,徽州女人的现实意义在于,徽州女人故事中没有一个坏人,她盼夫是自觉自愿的,没有人强迫她.这部戏原始质朴,没有污染,这是最能打动现代人的.说到过去,就用"封建糟粕"一棍子打死,固然不对,并可能是"十分粗浅"的;而以为过去就是原始与质朴,还能打动人,恐怕也有些武断.艺术家大概喜欢审美的看人生,因此,能从35年活寡中发掘出美来,这是艺术家的权利.比如,艺术家还可以从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发掘出美来,这故事讲一个守寡的女人,每天夜里在黑暗中...
· 微州文化—微州印象—无梦到微州
游过山,玩过水,看过牌坊和祠堂,这才算到过安徽。安徽的山水拳头产品是“两山一湖”,除了刚与丹霞山结成兄弟山的黄山外,黄山的情人太平湖,全国保留着最多千年古刹的九华山,都是赏心悦目的入诗入画之地。山水之外,徽州古民居是谋杀摄影发烧友胶卷的首席“元凶”,宏村还评上了“世界历史文化遗产”。景区亮点:虽然这条线路的降价幅度只有100元左右,算不上什么。但是,安徽是一个无处不渗透着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旅游圣地,老子、庄周、曹操、包拯,朱元璋、胡适、华佗、周瑜等英雄的故事数也数不完;流淌过英雄血的垓下、淝水,怎可不去凭吊?还唱遍大江南北的,一代徽商胡雪岩的传奇,怎能不去听?古旧的徽州“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无论是有意或无意地曲解了汤显祖的原意,这句诗已成为到徽州旅游的大招牌。在安徽省南部的黟县和歙县附近,散布着许多明清古村落,随处可见百年以上的老宅。徽州的文化,当然不是一座老房子就能代表得了的。马头墙...
· 微州文化—徽州文学—微州文化—徽州文学—(2)
徽州文化是一个极具地方特色的区域文化,其内容广博、深邃,有整体系列性等特点,深切透露了东方社会与文化之谜,全息包容了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民间经济、社会、生活与文化的基本内容,被誉为是后期中国封建社会的典型标本。学术界对其的研究,至少经历了大半个世纪,80年代以后更趋火热,逐渐形成了一门相对独立的地方学--"徽学",被誉为是并列与敦煌学和藏学的中国三大走向世界的地方显学之一。徽州位于黄山脚下,古称新安,北宋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建徽州府,遂得名。范围包括今黄山市的歙县、黟县、休宁县、祁门县、屯溪区、徽州区及黄山区的一部分,以及现属于安徽省宣州地区的绩溪县、属于江西省的婺源县。徽州社会和文化是在南宋以后崛起,明清时达到鼎盛与繁荣,清末以后衰退的。历史上有纷呈的学派与流派,内容几乎涵括文化的所有领域。其文风昌盛、教育发达、人才辈出,自宋至清,徽州共建有书院、精舍等260多所;社学明初有462所,...
· 微州文化—微州印象—徽州旅游全攻略之地理交通
古徽州,也就是今天的黄山市,它位于安徽省的东南角,与浙江和江西相连。黄山市由三区(屯溪区、黄山区、徽州区),四县(歙县、黟县、休宁县、祁门县)和黄山风景区组成,市府所在地设在屯溪。屯溪是黄山市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来黄山的游客的集散地,铁路黄山站,民航黄山站都设在屯溪。铁路与上海、南京、济南、北京、桂林等地相连。飞机则与武汉、上海、汕头、合肥、广州、北京、青岛、郑州、香港、宜昌、桂林、西安、济南、珠海等地开通航线。由于黄山市政府所在地屯溪就交通比较便利,所以到徽州旅游的人一般都是先到屯溪。屯溪到黄山市各主要景点的距离如下:1、屯溪到各大景点的距离:屯溪100KM黄山风景区屯溪30KM歙县屯溪60KM深渡屯溪120KM翡翠谷屯溪27KM棠樾牌坊群屯溪30KM唐模屯溪33KM齐云山屯溪60KM黟县西递30KM黟县宏村20KM黟县南屏屯溪150KM太平湖屯溪250KM九华山2、屯溪至市内各景区里程...
关于我们

关注族谱网 微信公众号,每日及时查看相关推荐,订阅互动等。
APP下载

下载族谱APP 微信公众号,每日及时查看

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