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失语症”与文化研究中的问题
胡适多年前说过的一句老话“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一直被当作使学术回避现实斗争的遁词而受到批判。然而现在想来,这话所倡导的那种既是实用主义、也是实证主义的学风,毕竟对纠正学术研究脱离实际问题抽象议论的风气是有裨益的。当今中国文艺学和文化研究发展得蓬蓬勃勃,但就所研究的问题而言,也存在着不少需要重新审视的地方。其中有些东西不仅是理论概念的问题,也是更具普遍性的研究方法和态度问题,需要我们关注。
一
在我看来,当今的文化研究中有一些理论和观念的确需要从现实问题出发进行重新审视。其中之一就是吵吵了不少年头的“失语症”。这些年来文化研究中所说的“失语症”是指由于西方学术理论、观念和概念大量侵入中国学术研究的话语中,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甚至堆砌外来术语,越来越多地谈论西方理论和观念,似乎找不到表达中国本土经验的语言了,于是被称为患了“失语症”。在许多学者看来,“失语症”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剩下的问题只是如何应对和治疗这个病症。
凭印象看,这个观点大致是不错的。但如果我们真正研究一下这个观点提出的实际背景,就会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了。中国学术界大量引进西方的新方法、新观念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即所谓“新方法年”以后的事。“失语症”的提出也是在此后,是90年代前期提出的。按照这个时代背景来看,“失语症”指的就是自西方的新方法和新观念引进后造成的我们自己原有的话语的失落。但仔细想一想,在此之前我们自己“原有的”话语是什么呢?就文艺学而言,此前的理论话语基本上是苏联的毕达科夫传授的几个概念,我们关于文学问题的谈论是在“阶级性与人性”、“真实性与倾向性”、“进步性与反动性”、“个性与共性”等几组抽象范畴中进行的。这还不算“两结合”和“三突出”的时代。这就是我们表达自己的、“本土”的文学经验的话语吗?相比之下,潜意识的象征、原型意象、孤独与荒诞感、影响的焦虑、召唤结构、叙述视角、期待视野等等西方来的新概念难道只是在剥夺我们“原有”的经验而没有为我们表达自己的文学经验提供一点新的工具与可能?严格地讲,如果说我们的文艺学研究中存在着理论话语不能表达文学经验的“失语症”,那么它是出现在新观念到来之前而不是之后。恰恰是在接受了许许多多的新观念后,我们才发现了表达自己真实经验的更多可能性,也由此而产生了对不能充分表达经验的焦虑。无论在引进新观念、新概念中产生了多少食洋不化的概念游戏,毕竟我们正是从这时开始才意识到了话语与经验之间的关系与矛盾的问题。
再进一步说,如果我们把“失语症”的问题向前推,从更早的文化和话语中寻找表达真正属于中国“本土”文学经验的语言,比如说传统的文学批评语言,那又怎么样呢?当今有的学派的确在进行着这样的努力。然而这样一来却可能发生另外一个问题:我们现在的文学经验是否是古代文学批评语言所能表达的?我们在谈论西方语言的影响时,有时会忽略了一个更基本的事实:语言影响的背景是文化影响,我们的“本土”经验中早已越来越多地羼入了西方文化带来的新经验。事实上从鸦片战争以后,文学和文学理论所面临的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传统的语言无法表达新的来自西方文明的经验。可以说那才是真正的失语现象,换句话说,我们所缺失的是表达新经验的新话语。也正因为如此才产生了从黄遵宪到新文化运动的语言革命。
二
90年代以来与“失语症”观点桴鼓相应的是后殖民主义理论,即认为当代的文化现实是西方文化处在中心统治地位,发展中国家则处在“边缘”,由此而形成了不平等的文化殖民与被殖民的关系。这种文化关系的一个重要表征就是西方话语的中心地位和对其他话语的影响、控制乃至剥夺的权力,即所谓“话语霸权”。“失语症”通常就被解释为西方“话语霸权”对中国本土话语的剥夺。
如果我们考虑到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文化同西方文化对抗的历史,要说西方文化在对中国文化行使着或企图行使某种“霸权”,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事。由此而进一步得出关于“话语霸权”的见解,即认为中国今天的话语中所充斥的西方话语,也是西方文化霸权在语言活动中的表现,似乎也是言之成理的。
这个言之成理的观点究竟符合不符合事实呢?当我们看到自80年代“新方法年”、“新观念年”以来大量涌现在批评和理论著作中的新词汇时,可能不得不承认事实确是如此。但如果认真分析一下,就会发现问题要复杂得多。问题首先在于,这个“话语霸权”的基本内容是什么?人们可能会笼而统之地把所有来自西方的话语统统纳入“霸权”之列,但作为当代文化现实的“西方”本身也是个庞杂的矛盾复合体,其中包含着主流的和非主流的各种各样的文化关系。即使是今天正在你死我活地拼杀的犹太教和穆斯林,从文化渊源来看也是与基督教的西方在同一个文化历史过程中相互影响发展起来的。显然,当我们说西方的文化霸权时,所说的“文化”指的当然是占统治地位或主流地位的文化而不可能是“整个”西方文化,当然更不是什么个别的支流、非主流甚至反主流的文化倾向。
然而回过头来看看近年来中国文学与文化批评的话语,很容易发现所使用的理论、观念和概念中其实没有多少是西方的主流话语。比如90年代以来在中国最为流行的以“后”字为前缀的一大堆概念――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等,基本上是法兰克福学派和其他非主流学术的概念。自萨义德、亨廷顿进入中国以来,中国学者们所津津乐道的文化冲突理论都是当今理论界的热门话语。这些显然不可能是西方的主流话语。反过来说,西方学术中的真正属于传统的、主流的学术话语,比如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实用主义等,却似乎在中国从来就很少有影响,更谈不到什么“霸权”。
从更广义的话语来看同样存在着这样的情况。人们在谈到西方尤其是美国文化的影响时,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好莱坞。由于好莱坞在世界各地观众中的广泛影响和在发行上的骄人业绩,它已成为美国话语霸权和文化殖民的象征。但这个好莱坞在中国文化中的命运到底如何,人们是否仔细地研究过呢?好莱坞电影所体现的美国式的价值观念,是否真的形成了“话语霸权”?
如果说好莱坞电影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曾无条件地成为中国普通观众心目中最好看的电影,《魂断蓝桥》、《音乐之声》成为一代人的情感寄托,那应当说不是什么“霸权”,而只是因为人们的电影欣赏经验太贫乏的缘故。到了80年代后期乃至90年代,观众的口味就越来越多地转向了香港、台湾和日本影片。周润发、成龙、周星驰等香港明星在一般大陆观众心目中的地位越来越超过了好莱坞的传统明星如格里高利・派克和奥德丽・赫本之类。只是到了90年代后期,随着以分账方式引进美国“大片”之后,人们才重新对好莱坞发生了兴趣。这次人们的兴趣主要集中在所谓的“大片”上,即那些用巨额投资以高科技的手段制作出来的以惊人效果和豪华场景取胜的影片,如幻想、灾难、恐怖、战争、警匪和政治黑幕等题材的影片。
好莱坞电影是否把美国的价值观念“殖民”到了中国其实是个疑问。有些典型地体现了美国人的价值观念的影片在中国并不一定有多大影响。比如在最早一批进口“大片”中,以高科技手段制造惊人视觉效果的影片如《真实的谎言》、《生死时速》等获得了普遍的成功;而像《阿甘正传》这样典型地体现了美国式价值观念的电影,影响就远不如那些具有惊人视听效果的影片。好莱坞有些描写小人物对抗政府甚至总统的政治影片如《摩羯星一号》、《迷幻追踪》等,体现了美国式的自由与个人价值信念。而在中国的接受中,这些影片却常常被当成了揭露美国社会黑暗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活教材,也就是说被误读了。好莱坞“大片”中真正吸引中国观众的豪华场景和惊人特技效果并非美国文化独有的,实际上在中国与世隔绝的60年代所拍摄的电影中,也不时地会冒出类似好莱坞式的华丽场景(如《女跳水队员》)、惊险特技或用平行蒙太奇制造“最后一分钟的搭救”效果(如《铁道卫士》),当然由于经验、技术和其他方面的限制,使这些效果比起真正的好莱坞电影来显得简单粗糙罢了。这说明,好莱坞电影的视听效果与其说是美国文化特有的性质,不如说是人类普遍的心理和趣味需要更为恰当。好莱坞的“大片”的确在近年来征服了中国的电影观众,但这种征服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因为技术意义而已,并非真正文化和价值观念方面的征服;至于这种“征服”是否可以造成某种单一话语的“霸权”和特定文化的“殖民”,恐怕是个很可疑的问题。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感谢每一位辛勤著写的作者,感谢每一位的分享。

相关资料

- 有价值
- 一般般
- 没价值








推荐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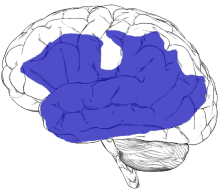
关于我们

APP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