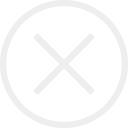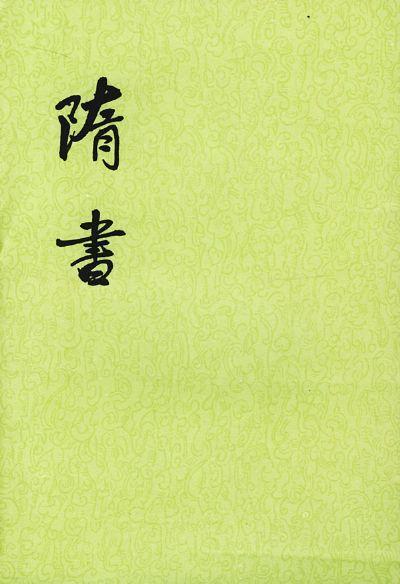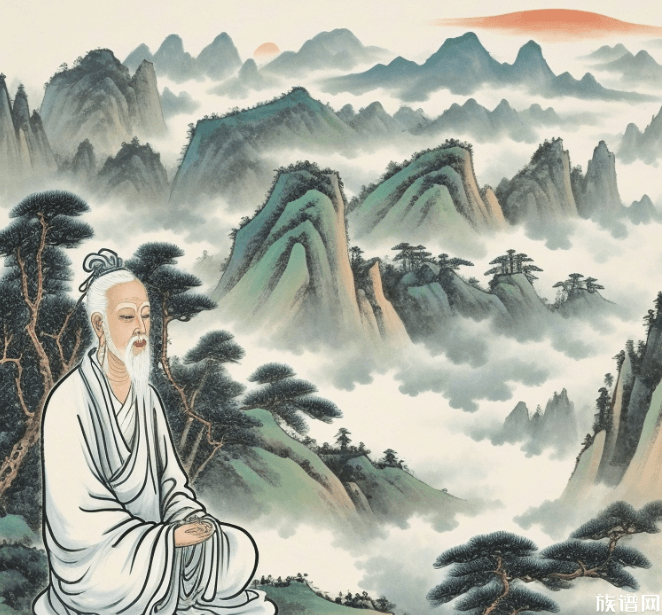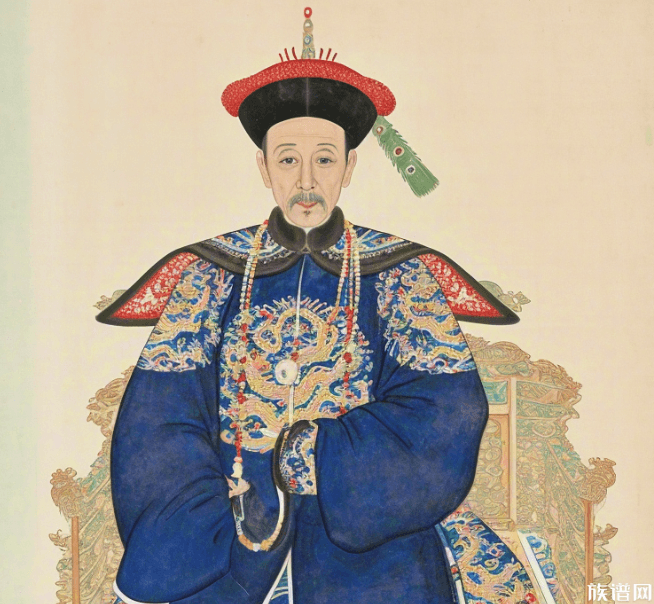牛敬飞,男,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2012年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毕业,本文出自其博士论文《五岳祭祀演变考论》。
博士导师: 清华大学教授 秦 晖
通讯评委: 清华大学教授 张国刚 中华书局编审 陈 虎
开皇九年(589年),隋平南朝,朝野请封禅,文帝弗许。六年后,以晋王杨广为代表,朝廷再起封禅之议,隋文帝先命牛弘等人草拟封禅礼仪,最后出于谨慎仍未行封禅,但其提出:“但当东狩,因拜岱山耳”。开皇十五年(595年),隋文帝至泰山行巡狩之礼,其礼制为:“为坛,如南郊,又壝外为柴坛,饰神庙,展宫悬于庭。为埋坎二,于南门外。又陈乐设位于青帝坛,如南郊。帝服衮冕,乘金辂,备法驾而行。礼毕,遂诣青帝坛而祭焉。”大业四年(608年),隋炀帝北巡恒山,行巡狩之礼,“其礼颇采高祖拜岱宗仪,增置二坛,命道士女官数十人,于壝中设醮”;大业十年(614年)炀帝“过祀华岳,筑场于庙侧。”史臣评炀帝礼恒山、华岳为不经之礼:“事乃不经,盖非有司之定礼也”(以上俱见《礼仪志》)。但仔细对比三条记录,可知炀帝礼恒山是遵从文帝礼岱宗之制的,礼西岳“筑场于庙侧”亦当如此,并非无定礼。笔者以为唐人所说“不经”主要针对隋代擅行巡狩五岳之礼。
巡狩之礼源自《尚书》,秦皇汉武曾因模仿上古帝王巡狩山川而闻名,但此二帝巡狩或未有定制。至东汉章帝,“巡狩”为白虎观会议之重要议题,事后不久,元和二年(85年)章帝即巡狩东方,“幸太山,柴告岱宗”(《后汉书·章帝纪》),之后安帝亦行之。秦汉时代,泰山封禅礼风靡一时;进入东汉,儒学昌明,故此时有经学依据的“巡狩”之礼为朝廷注意。汉武帝议封禅时儒生即提出据《尚书》《周官》制礼;郑玄解释三礼曾用“天子巡狩礼”(《毛诗正义》),王应麟以该礼为汉代之逸礼(《玉海》卷39),汉人解经若有所本,则可判定至少至东汉中期,朝廷已据礼经定巡狩之礼。
《白虎通》引《尚书》,指出巡狩至于五岳,须在五岳祭天。东汉以降,华夏分裂,再无帝王于五岳行巡狩祭天之礼,直至隋朝统一,隋文帝才勉强为之。现就隋文帝巡狩礼做出解析。首先,巡狩礼地点在山下岳庙附近,而非山顶,此即区别于封禅礼。其次,巡狩有祭天柴坛。《白虎通》:“巡狩必祭天,何本?巡狩为祭天告至,《尚书》曰‘东巡狩至于岱宗柴’也”,此是汉人宗上古巡狩祭天之事;《礼记》“天子适四方,先柴”郑玄注:“所到必先燔柴有事于上帝也”(《十三经注疏》),此是汉人理解周代巡狩,由此可知汉人欲复巡狩当有燔柴告天之礼。隋行巡狩立柴坛当本于此。
再次,隋代巡狩礼最具特色的便是仿南郊修青帝坛,此坛为祭祀中心。隋制为何要修坛祭祀?东汉章帝巡狩时“有黄鹄三十从西南来,经祠坛上”(《后汉书·章帝纪》),这是汉代巡狩礼残留之吉光片羽,其经中古战乱至隋代早已不存,故寻修坛源头只得再从礼经入手。与天子外出行巡狩礼相反,诸侯因时会殷同有朝觐礼。《仪礼·觐礼》有“诸侯觐于天子,为宫方三百步,四门坛十有二寻,深四尺”,据此古制诸侯觐礼有坛。郑注《周礼·大宗伯》也以为诸侯朝觐天子皆立坛,并提出:“十二岁王如不巡守,则六服尽朝,朝礼既毕,王亦为坛合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守”,此是郑玄以为王出巡狩与诸侯入朝时王之命政礼属同类,巡狩筑坛应符合其义。郑注《秋官·司仪》:“合诸侯,谓有事而会也。为坛于国外以命事,宫谓壝土以为墙处,所谓为坛壝宫也。……《觐礼》曰:‘诸侯觐于天子,为宫方三百步,四门,坛十有二寻,深四尺’是也,王巡守,殷国而同,则其为宫亦如此与?”此是郑玄推断巡狩礼与觐礼之宫坛建置类同。三礼之学自魏晋出现郑王之别,北朝郑学盛行,又特重恢复周代制度,如北周即主“姬周”。隋继北周,承其风气,其开国制礼核心人物牛弘、辛彦之皆为北周陇右人士;此二人参与拟定开皇封禅礼,文帝虽未封禅而行巡狩,而巡狩相关礼仪亦当由二人制作。当时未有既成巡狩礼可参考,郑注三礼应成为当然选择。既然郑玄曾见汉巡狩礼且推断巡狩礼应立坛会诸侯,隋臣则极有可能用郑义为巡狩立坛。
至于为何仿南郊而立青帝坛,则又要回到郑玄礼学。北朝在郊祀制度上更倾向郑玄五精帝六天之说,故郊丘分立,正月于南郊祭感生帝。感生帝本质是五精帝之一,五精帝之礼与南郊祭感生帝之礼有可以趋同之依据,隋初制礼之臣或许就持这一态度。于是在制定巡狩礼时,要满足礼经所说祭天,隋代现有祭天坛制只有圜丘与南郊,巡狩非封禅大礼自然不能用圜丘之礼;同时南郊所祭感生帝本质又属五精帝,隋礼又直称南郊所祭为“感帝赤熛怒”。(《隋书·礼仪志》)于是为方便起见,隋臣便于泰山下仿南郊坛制立青帝坛,其燔柴所告之天也即青帝灵威仰。依此类推,炀帝巡狩恒山所祭之神当为玄帝协光纪,巡狩西岳所祭之神当为白帝白招拒,两次均按五方致礼。
此外,从隋文帝巡狩礼舆服来看,“衮冕”是当时最高级别服冕,其适用于祀圜丘、方泽、感帝、明堂、五郊等等。(《隋书·礼仪志》)巡狩泰山所祭青帝即属五郊,故文帝用衮冕。之后炀帝复周代服冕,于衮冕上再制裘冕以分文帝衮冕功能,裘冕专用于“圜丘、感帝、封禅、五郊、明堂、雩、蜡”等大祀,以应《周礼·司服》“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是可推知炀帝巡狩恒山、华岳或用裘冕。《周礼·春官》记玉辂以祀,金辂以宾以封,隋制亦规定金辂“朝觐会同、乡射饮至则供之”(《隋书·礼仪志》),巡狩即会同四方诸侯,《隋书·礼仪志》记文帝巡狩用金辂符合《周礼》以宾以封之义。又天子之驾,法驾仅次大驾,汉制“大驾祀天,法驾祀地,五郊、明堂省十三”(《汉官六种》),《礼仪志》记文帝用法驾礼青帝切合古礼。
最后,隋代二帝巡狩皆有赦文,符合大祀行赦传统。《隋文帝拜东岳大赦诏》有“朕以不德,肃膺鼎运,上承昊天之命,仰述圣人之道,思使含生之人,咸敦礼义;率土之内,同致雍熙。”文帝此意完全符合汉人所释巡狩,即“道德太平,恐远近不同化,幽隐有不得所,故必亲自行之,谨敬重民之至也。”《隋炀帝巡幸北岳大赦诏》记有:“飨帝禋宗,虔奉明祀”,此能印证其巡狩所祭为玄帝协光纪;在表达推行王化时,该文还突出巡狩礼会同华夏诸侯之义:“长城作固,镇隔华戎。率彼子来,亲巡玄朔。既而南辕肆觐,北岳升柴,继绝代之遗风,弭之盛典。”(两诏俱见《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
综上所述,可以推定,牛弘等人在巡狩祭天理念上采用了郑玄五精帝之义,在议定巡狩坛制舆服上严格遵循了郑注三礼,特别是《周礼》。牛弘不惟制定文帝巡狩泰山礼,且负责炀帝巡狩恒山礼(《隋书·牛弘传》),于是便出现《隋书·礼仪志》所说“其礼颇采高祖拜岱宗仪”。
需要指出,隋代国祚虽短,但在礼制建设上却颇有建树,恢复湮没多年的巡狩五岳礼便是其礼制创新之一。参考《大唐开元礼》可发现,玄宗所制巡狩礼坛制与隋朝大体一致(《大唐开元礼·皇帝巡狩》),只是所祭之天由五精帝变成了“昊天上帝”,《开元礼》上承显庆、贞观礼,或许其巡狩礼制正是源自唐初史臣诟病的隋朝巡狩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