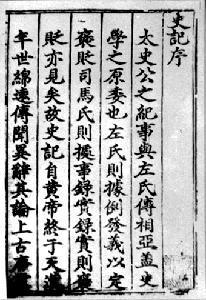八卦起源占卜(数卜)论分析
摘 要:本文对流行于学术界的八卦起源占卜论及各种与之相关的材料、认识作了具体深入的辨析,认为八卦起源于占卜(或数卜、龟卜、卜筮)的观点和认识是无根无据的。八卦并非由数字卦发展而来,更非源于龟卜、数卜。数字卦的存在是以八卦六十四卦的存在为前提,它们只是利用八卦六十四卦进行占筮而得到的一种结果(卦象及筮数),而商周龟甲及史前墓葬龟甲也都与数字卦的产生无关,更与八卦六十四卦起源无关。
关键词:八卦起源 占卜论 数字卦 龟甲
八卦起源于占卜或数卜是学术界最普遍和流行的一种观点,或可谓主流认识,如:冯友兰认为八卦由模仿占卜的龟兆而来,是标准化的“兆”;高亨认为八卦中的阴阳爻象征占筮用的两种竹棍,八卦是有节和无节两种竹棍的不同排列方式;李镜池认为阴爻和阳爻象征古代结绳记事中的小结和大结,古人用结绳方法记录占筮之数,后来衍化为八卦。由于“诸种假设均缺乏文物验证”[1],所以它们现在只是成为一种历史记忆和资料。
在当代,由于殷周数字卦的发现和破译,八卦起源于占卜或数卜的观点似乎有了考古依据和线索,所以易学界比较重视这种新的发现,在认识上可能更加倾向于八卦起源卜筮论,如:唐明邦先生认为张政1980年提出八卦由古代数卜记录符号演化而来,“这一发现对探讨八卦起源,筮数同卦象的关系,打开了新思路”[2]。郑万耕先生认为冯友兰、高亨、李镜池等人的卜筮说乃至章太炎、钱玄同、郭沫若等人主张的八卦起源生殖器说“都是无从确证的猜测”,而张政的理解虽“仍属猜测,但它具有相当的考古文献上的根据,为我们探讨卦爻画的起源,开辟了新的途径”[3]。陈咏明先生一方面认为张政对殷周数字卦的破译与朱自清关于八卦符号源于数卜、数目的推想相印证,同时又说“八卦的形成、发展和运用,都是为了占筮,须从占筮的角度去把握,方不致偏离方向”、“由于人类社会的发展,生活内容日趋复杂,即使可以增加内涵,八种卦象也不足以包括所占之事和事物的变化了,于是加以推衍,成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于是卦象涵盖的内容加多应付的事变也加多”[4];朱伯昆先生在四卷本《易学哲学史》中有类似的说法:“……八卦所以演为六十四卦,看来是出于占筮的需要。随着占筮的发展,八种卦象不足以包括所占之事,于是加以推衍,成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便可以应付无穷事变了”[5]。
在此,我们有必要看看有可能支持八卦起源占卜论的考古材料以及考古学家的相关认识,并对它们试作进一步的思考和分析:
张政先生统计周初32例数字卦共有168个数字,涉及一至八字,其出现次数分别为:一,36次;二,0次;三,0次;四,0次;五,11次;六,64次;七,33次;八,24次。以六、一两字出现次数最多,分别为64次和36次,而二、三、四都是0次。他认为这是个必须注意的现象:“易以道阴阳,阴阳不成对还有什么易理可讲?”但是将所有奇数出现的次数加起来,其和为80(36+0+11+33),将所有偶数出现的次数加起来,其和为88(0+0+64+24),二者大体平衡。所以他认为二、三、四这三个数字虽不见,但实际上还是存在的,推测应是二、四并入六,三并入一所致。古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古汉字的数字从一到四都是积横画为之,一二三自上而下书写起来容易彼此掺合,极难区分,因此将二、三、四从字面上去掉,归并到相邻的偶数或奇数之中,“所以我们看到六字和一字出现偏多,而六字尤占绝对多数的现象”。于是他推论:“占卦实际使用的是八个数字,而记录出来的只有五个数字,说明当时观象重视阴阳,那些具体数目并不重要。这是初步简化,只取消二、三、四,把它分别向一和六集中,还没有阴爻(--)、阳爻(―)的符号”[6]。张先生这里的分析是很细致的,但最后一句话却模棱两可或者也可能隐含着一种错误的认识,而后来的学者也瑕疵莫辨,引以作八卦起源卜筮论的依据。张先生说“这是初步简化,只取消二、三、四,把它分别向一和六集中,还没有阴爻(--)、阳爻(―)的符号”,这是就考古材料和当时所见阴、阳爻画存在的年代就事论事,是符合实际的,但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八卦符号的阴阳爻画是由数字卦的六(∧)、一两个数字发展而来,或者张政先生本人也有此意,但它在学理上是讲不通的:“易以道阴阳,阴阳不成对还有什么易理可讲?”、“……说明当时观象重视阴阳,那些具体数目并不重要”,这些论述的大前提是数字卦中的所有数字都被区分为阴阳二性,是阴、阳的象征和代表,张先生对32例数字卦168个数字的统计、分析也证明这个思路和理解是正确的、合理的。所有数字被区分为阴阳二性的三爻数字卦、六爻数字卦(即张先生和学界所论商周数字卦)必然意味着阴、阳爻画的三爻八卦、六爻六十四卦的存在,而且它们是先于数字卦的存在而存在,而数字卦只是用阴阳爻画的八卦、六十四卦进行占筮而得到的筮数(虽然,当时或现在我们并没有看到阴阳爻画的八卦、六十四卦符号在商、周时期的存在或普遍存在――实际阴阳爻画的八卦、六十四卦符号在商周之前是存在的,已出土新石器时代考古资料中有丰富的相关资料,对此拟另作分析和释读)。简言之,认为八卦符号源于上古占筮记录的数字符号,阴爻(--)、阳爻(―)来自商周数字卦的六(∧)、一两个数字[7],这完全是颠倒了二者的关系,倒果为因。如果没有阴、阳爻画八卦、六十四卦的存在,张政先生对32例数字卦168个数字的分析、理解又何从谈起?至于商周、秦汉时期一至八8个数字向六、一两个数字的归并倾向以及最终只用六、一两个数字,不妨看作是数字六(∧)、一与八卦符号阴爻(--)、阳爻(―)画法接近的缘故,长沙马王堆帛书《周易》六十四卦的画法实际是阴阳爻画八卦符号而不能视为数字卦(阴爻画作“∧”而不作“--”,显然与阳爻更容易区分,而不致因两条断线连在一起或过于接近而让人误识为阳爻“―”)。
张亚初、刘雨先生在稍后于张政发表的文章中,也搜集了36例商周数字卦材料(其中包含几例用三条断线和一条连线组成的四爻、五爻卦符,他们认为是与杨雄《太玄经》有关的资料,如有的可释为《太玄经》的“争首”、“锐首”,同时也是“我国目前所见的最早的卦画”,而张政、冯时先生则认为应是六爻卦符的简省,略当后世易家所讲的“互体”[8]),并说“上述三十六条材料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数目字的组合,而且都是由三个或六个数字构成的组合。这不能不使我们与导源于数卜的我国古代占筮法――八卦联系起来。八卦的每个卦由三个爻(单卦)或六个爻(重卦)组成,每个爻也都是可以用数字来表示的”。至于当时“是否有卦画,尚不得而知”[9]。张亚初、刘雨两先生是直接认为或判断八卦符号“导源于数卜”,并未作论证。关于“导源于数卜”,他们作注曰:“《左传》僖公十五年:‘龟,象也;筮,数也’。说明龟卜,吉凶表现在龟甲裂纹所成的象上。用蓍草来筮,吉凶表现在蓍草成卦所得的数上。《考古》1976年4期,汪宁生同志在《八卦起源》一文中,又从民族学的角度找到了数卜的例证”。这段话是否证明或说明八卦起源或“导源于数卜”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筮,数也”说的是八卦筮法,根据占筮所得的卦象及据以画出卦爻的筮数(分阴阳)来判断吉凶,如《周易・系辞》“大衍筮法”即如此,所以《左传》这段话并不表示八卦“导源于数卜”,更谈不上证明。汪宁生先生《八卦起源》一文谈到的有关数卜之民族学资料,有的与八卦无关,有些则与八卦相关:如西盟佤族“司帅报克”占卜法,“其法是用小木棒在地上随便划许多短线条,然后计其总数,看是奇数还是偶数,奇数主凶,偶数主吉”,这种方法与八卦没有关系。汪宁生认为与古代筮法最相似的要算四川凉山彝族“雷夫孜”占法,其方法是:“毕摩(彝族巫师)取细竹或草杆一束握于左手,右手随便分去一部分,看左手所余之数是奇是偶。如此共行三次,即可得三个数字。有时亦可不用细竹或草杆,而用一根木片,以小刀在上随便划上许多刻痕,再将木片分为三个相等部分,看每一部分刻痕共有多少,亦可得出三个数字。然后毕摩根据这三个数是奇是偶及其先后排列,判断打冤家(过去彝族奴隶主操纵下一种械斗、出行、婚丧等事。”汪先生以为数分二种而卜必三次,故有八种可能的排列和组合;用一画代表奇数、二画代表偶数,此即阳爻(―)、阴爻(--)的由来;把奇数和偶数八种可能的排列情况,分别用这两种符号画出来,这就是八卦的由来。汪先生据此认为八卦起源于数卜,其实也是倒果为因:无论细竹(草杆)法或小刀刻木法,得到的都是阴阳爻画的八卦(以偶、奇代替阴、阳爻画)而非数字卦(如前所述,数字卦存在的前提也是阴阳爻画八卦、六十四卦的存在),它只是一个起卦过程、利用八卦符号进行占筮的过程(如《周易》“大衍筮法”一样)而不证明八卦起源于数卜,所谓古代筮法如“大衍筮法”正是对八卦(六十四卦)的利用而不说明八卦起源。汪先生文中所言及四川阿坝地区藏族用牛毛绳八根打结、羌族用数麦杆法、云南傈傈族数竹竿33根等占法,语焉不详,但以占卜三次而数分奇偶而论,其法都应该是对八卦的利用而不说明或证明八卦起源。这里还有必要指出,汪先生说“八卦原不过是古代巫师举行筮法时所用一种表数符号”是错误的说法:“雷夫孜”等占法按操作程序一次得出或奇或偶之数,如用阳爻(―)或阴爻(--)表示,或可认为这阳爻、阴爻乃是“表数符号”,但操作三次所得之八卦符号(或用“奇奇奇”代表乾卦,“偶偶偶”代表坤卦等)却不是“表数符号”,八卦并非数(虽然起卦过程中要用到数、产生一些数)。汪先生文中也说古人占筮“感到八种卦象太少,于是将八卦相重衍变为六十四卦,揲蓍之法也愈演愈繁,要经过‘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意即六十四卦亦“导源于数卜”,这当然也是不足为训的。张政先生在新石器时代崧泽文化中发现八个六爻数字卦,如有三五三三(遁卦)、六二三五三一(归妹卦)等[10],按汪宁生先生的推测,至少阴阳爻画的三爻八卦在崧泽文化中已产生(否则不必或不可能有六爻数字卦),这自然也否定八卦符号起源于商周数字卦、数卜的说法。
徐锡台先生在张政先生研究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说:早在原始社会崧泽文化中已出现数字卦,由一、二、三、四、五、六这六位数字排列组合而成。这种数字卦经过千年的使用,进入商周时期人们省去积画二、三、四这三个数字,增补了七、八、九这三个数字,即用一、五、六、七、八、九这六位奇偶数字排列组合成重卦。进入战国中期又省去五、七等两位数字,只剩下一、六、八、九四位数字;至西汉文帝十五年又省去八、九两数只剩下一、六,如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汉墓竹简上的易卦;至汉武帝时期,由于篆字改为楷字,故将“∧”垂直成阴爻符号,实际上阴阳符号仍是一、六两位奇偶数[11]。徐先生这里的论述和认识有许多似是而非的东西:其一,崧泽文化数字卦出现一、二、三、四、五、六这六位数字是仅就张政先生例举的两个数字卦而言,并不能确定原始社会的数字卦就只使用这六个数字,所以认为由原始社会使用一、二、三、四、五、六这六个数字发展到商周时期使用一、五、六、七、八、九这六个数字没有确定可靠的基础和依据。其二,商周数字卦现一、五、六、七、八、九这六个数字并不意味着占筮时不使用或不出现二、三、四这三个数字;如前所述,这三个数字仍然是要出现和使用的,只是因为这三个数字与一都是积横画而为之,画数字卦时上下重叠容易互相掺和发生混乱,故占筮后画数字卦时将二、三、四分别归并到六、一两数之中。故徐先生认为的原始社会占筮用一、二、三、四、五、六这六位数字,发展至商周用一、五、六、七、八、九这六位数字,至战国中期仅用一、六、八、九这四个数,至西汉文帝仅用一、六两个数字,这种占筮所用数字的发展演变顺序是不成立的。其三,徐先生认为战国中期数字卦省去五、七,仅用一、六、八、九四个数,依据的材料是湖北江陵天星观楚墓竹简。据张政 先生统计、分析,天星观楚墓竹简上的易卦共有八组十六卦,所用数目字为:一,37次;六,49次;八,5次;九,4次;残缺,1次[12]。据此可知,天星观楚墓竹简易卦涉及占筮并非只用一、六、八、九这四个数,而仍然应该如其他商周数字卦一样,也使用了二、三、四、五、七等数字,只是在画数字卦时将后者按奇偶分别归并入一、六两个数字而已。故徐先生拟构的占筮用数从原始社会至商周至战国中期的发展演变顺序是不成立的。其四,张政先生提到四川理番县出土双耳陶罐上有两个易卦,一个秦代的为一八七一八九(离下,离上,离),一个汉代的为一六十(艮)[13]。这个资料同样不支持徐锡台先生拟构的占筮所用数字发展演变顺序。徐先生文中引理番县双耳陶罐易卦资料(且错为“九八七一八九”)以证其占筮数字发展演变顺序[14],当然也是不足为训的。总而言之,无论商周数字卦或是湖北江陵天星观楚墓竹简上的数字卦,其产生和存在的前提必然是阴阳爻画八卦、六十四卦的存在,那些数字只是利用八卦、六十四卦进行占筮而产生,而非八卦之源。当然,崧泽文化中的数字卦与四川理番县出土的数字卦也不例外(易卦中使用或出现不同的数字应该与占筮方法及对数字的归并方法有关)。而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竹简以及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上仅用一、六(∧)两数字的易卦,实际应是阴阳爻画卦的别一种写法,而非数字卦。
徐锡台先生认为商周时期人们以一、五、六、七、八、九这六位奇偶数排列组合成二百一十六个单卦,四万六千六百五十六个重卦,二十七万九千九百三十六爻,而六十四卦是在秦汉时才出现、在商周时期是不存在的[15]。这个认识是否正确呢?我们认为它是不正确的:其一,商、周数字卦出现一、五、六、七、八、九这六个数字,并不意味着占筮时只出现和使用了这六个数字,而是一至九这九个数字都有出现和使用,只是在画卦时将二、三、四这三个数字归并入六、一两数之中。若按徐先生理解,商周数字卦应是由一至九这九个数字排列组合而成,当远不止二百一十六个单卦、四万六千六百五十六个重卦以及二十七万九千九百三十六爻。同理,距今约5500年前原始社会崧泽文化中也当如此,因为其数字卦据公开的两条资料已出现一、二、三、四、五、六计六个数字,而且也可能使用了其他数字。故徐先生所论前提失据。其二,占筮是根据卦象、爻象或卦数、爻数来判断吉凶。商周数字卦若按奇、偶数归并为阳爻、阴爻,那么它反映的只是对六十四卦的一种运用,而不存在什么“四万六千六百五十六个重卦”之类。如果奇偶数不能归并、不应该归并,那么商周数字卦才会有成千上万、数十万乃至更多的卦爻,而且必有其存在的原因和理由,即占筮所需,如:一五六七八九、九八七六五一、五六七八九一、一九八七六五、一六七八九五、五九八七六一以及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九九九九九九、一一五五七七、一一七七五五、一七五一五一、一七一五一五等等,等等,均是不同的卦,表示不同的吉凶。成千上万的卦便表示成千上万种不同的吉凶,数十万卦爻便表示数十万种不同的吉凶(否则便没有存在的理由,而只能按阴阳、奇偶归并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当然这不会是商周数字卦的,更不可能是原始社会崧泽文化数字卦的及意思表达。其三,如前所述,徐先生所论占筮用数从崧泽文化的一、二、三、四、五、六到商周时期的一、五、六、七、八、九再到战国中期的一、六、八、九至汉代使用一、六两位数字,这种发展演变顺序是不成立的、不存在的,故徐先生所论商周时期有四万多个重卦、二十多万卦爻到秦汉才有六十四卦也是不成立,没有理据的。其四,无论商周数字卦或战国时期天星观楚墓竹简数字卦,都将二、三、四甚至还有五、七等数字按奇偶、阴阳归并入一、六两个数字,证明“观象重视阴阳,那些具体数目并不重要”,数字卦只是对阴阳爻画卦的一种运用,因八卦六十四卦用于占筮而产生,而非徐先生所论那样存在着成千上万的含义不同的数字卦。按徐先生的理解,一、五、六、七、八、九或其他数字,可以排列组合成成千上万种不同卦象和含义的数字卦,以供占筮判断吉凶时对号入座,那么古人就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将二、三、四等等数字归并入一、六两数。既存在归并,则判断吉凶所据必是阴阳爻画卦,只是用筮数表现而已。已知崧泽文化中的数字卦虽然没有将二、三、四归并入一、六两数,但它们显然也不可能是徐先生所论“四万六千六百五十六个重卦,二十七万九千九百三十六爻”那种数字卦。其五,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竹简及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上的易卦仅用一、六两数排列组合成六爻卦,实际即六十四卦,与商周数字卦、天星观楚墓竹简数字卦、崧泽文化数字卦等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是阴阳爻画卦的别一种写法(用其他任何两个不同的符号分别代表阴、阳爻,排列组合成六十四卦,其卦爻象、含义完全不变),后者是利用六十四卦占筮所得卦象及爻数。故徐先生认为“今本《周易》绝不是商周时期的作品,而是秦汉时代才出现的”也是无据。
张政先生曾经仿照《周易・系辞》“大衍筮法”试图改造筮仪,以便得到商周数字卦中的一至八或一至九这些筮数,但顾此失彼,不能成功。张先生又据敦煌卷子本《周公卜法》以及旧社会玩纸牌的方法摸拟,以64根筹码每次分四组废弃一组不用,其余三组分别揲之以八记录余数,重复一次便可得到筮数在一至八之间的六爻数字卦[16]。这个方法自然可以解释商周数字卦的来源,但我觉得数字卦的产生也可以依据其他的方式,如:将一把蓍草或竹棍(可固定为64根或100根等)随意取出若干根不用,然后揲之以八或揲之以九记录余数,重复六次便得到筮数在一至八或一至九之间的六爻数字卦。甚至筮数为十的卦爻(四川理番县出土汉代陶罐及《屯南》4352、风雏甲骨H11:235都有筮数为十的数字卦[17])也可根据诸如此类的方法得出。无论哪种方法,只要是求三位数字卦、六位数字卦而且数分阴阳,其前提都是八卦六十四卦的存在,筮占只是对八卦六十四卦的一种利用。当然原始社会崧泽文化中存在筮数在一至六之间或一至十之间的六位数字卦也就不奇怪了,而不必如徐锡台先生认为那样有数万个重卦、数十万卦爻乃至更多。管燮初先生分析42例数字卦,发现每卦均为六爻,一个卦的爻文至多四种没有例外,因而认为数字卦爻不仅分阴阳,而且还分老阴、老阳、少阴、少阳[18],这也证明数字卦存在的前提必然是阴阳爻画六十四卦的存在。李零、曹玮等先生认为数字卦的奇偶数之间,如一与五、七、九和六与八之间,不能简单的归并为阴爻与阳爻,不同的奇数之间或是偶数之间应有所区别,建议将筮数为一至十之间的数字卦称为“十位数字卦”(是否可以称“易”还有待证明),将汉代用六、一两数构成的易卦称为“两位数字卦”(“三易”),并且也“同意张政等先生主张的现在看到的周易是从早期的数字卦发展而来的观点”[19]。我们认为,这些认识也存在混乱和误解:汉代用六、一两数构成的易卦实际是阴阳爻画六十四卦的别一种写法,故不宜以“两位数字卦”称之,前已言明;所谓“十位数字卦”如徐锡台先生所理解的那样,它当然就不是阴阳爻组成的八卦六十四卦那种“易”,但无论商周数字卦、战国楚简数字卦或崧泽文化数字卦,其真相都不是徐先生理解的那样,而只是利用八卦六十四卦占筮所得筮数,故称“数字卦”亦可;无论商周数字卦、战国楚简数字卦,画卦时按阴阳、偶奇作了归并是事实,至于没有完全归并为六、一或其他两个奇偶数组成的易卦,那正是因为它们是“数字卦”的原因(前者实际是阴阳爻画卦,判断吉凶只能据卦象、爻象,而数字卦还可以依据各爻的筮数建立判断吉凶的方法,如常用的《周易》“大衍筮法”一样)。所以数字卦中“不同的奇数之间或是偶数之间应有所区别”这个判断当是合理的甚至正确的,其存在的原因或理由正应该是可据各爻筮数作进一步的推断或有不同的判断吉凶的方法,而不是证明阴阳爻画卦由数字卦发展而来。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感谢每一位辛勤著写的作者,感谢每一位的分享。

相关资料

- 有价值
- 一般般
- 没价值








推荐阅读

关于我们

APP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