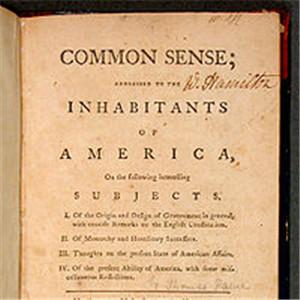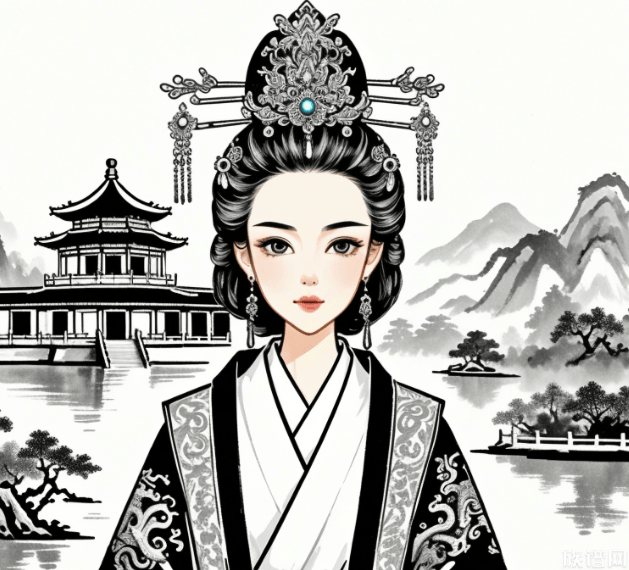卫氏祠堂与一个老人有着情丝万缕关系
如无意外,在每天上午七八点,卫氏大宗祠的侧门都会准时打开。这座占地1900多平方米、历经400年沧桑的祠堂,迎来一位每天如期而至的老人。

他是这座祠堂最重要的客人,同时也是它的“主人”。他叫卫本立,77岁,现在他的身份是卫氏大宗祠管理委员会名誉会长。他每天的生活与别的老人一样,早上起来喝早茶,上午悠闲地踱到码头旁的公园,与其他老人们打打麻将,回头下午再战。唯一的不同在于,喝完早茶后他总要来大宗祠里坐坐,点上香,然后翻看他自己编纂的族谱。这部族谱由他一字一句写在泛黄的纸上,装订为一本,他每天都会拿出来细细翻阅,就像在完成一件意义非凡的仪式。
这位名誉会长每月能收到管委会的两百元酬劳,原本有四百,后来他把其中两百给了她女儿。本来他领这四百元酬劳是要负责整个祠堂的日常维护的,后因年纪大了身体不便,就把一些像打扫卫生之类的工作交给他女儿来做。现在她女儿成了祠堂名义上的管理员,隔三差五地也要往祠堂跑。
当我们初次见到卫本立时,他正坐在祠堂大殿下的圆桌上。这里曾是清明节宗族聚会的聚餐之处,那时摆着近三十桌宴席,有舞狮队表演庆贺,头顶悬挂着大红灯笼,族人们觥筹交错,好不热闹。现在偌大的厅堂只有卫本立一个人,坐在圆桌的一角,摆上一壶茶,抬头就能望见象征卫氏宗族皇亲国戚身份的“燕子斗拱”。
卫氏大宗祠
他早已是一个名人了。处于城中村改造进程中的沥滘,以“华南最大古建筑群”的名头吸引了社会媒体的广泛关注。作为这座村落中仅存的“族老”之一,凡是跟卫氏大宗祠有关的话题都离不开卫本立。每当有媒体来访,他便会带他们来参观祠堂,讲解光辉的历史,然后坐在这张圆桌旁接受他们的提问。
对卫本立来说,媒体的来访往往意味着事情朝不好的方向发展。例如当沥滘列入改造规,一些祠堂要被“保护性迁建”,一座祠堂被开发商深夜强拆,改造方案的通过率超过50%等等。这时候沥滘还残留着的这十二座祠堂就又被卷入,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一时又有文博专家为保护这些祠堂鼓与呼。
这些对于卫本立是常识的东西,对于媒体而言却是新闻。他几乎从不拒绝媒体的采访,甚至在族人看来他“太会说”了一点,凡是遇到跟祠堂有关的问题,村里人就会说:你们去找卫本立吧,他可能说了!
卫润德就不一样。这位曾经做过卫生所所长的81岁老人,现在被村里人认为是卫本立外唯一的“村史通”。他的儿子开了一间卖医疗器械的临街店铺,卫润德没事就在那待着,帮儿子看门面。我们与他之间曾有过几次愉快的访谈,但当临走前最后一天前去探望时,他竟变得十分不耐烦。
“没用的,你们现在问这些,在网上你们敢不敢说这些话?”他以一种十分懊恼的语气说道,“城中村改造不是一件好事来的,都改了,没乡情了。这些都起了大楼,海外的回来参观还能看什么?”“这又拆那又拆,就是为利益咯!”
我们想插嘴,但他似乎不给我们机会,“这些都是文物啊,家说你那些是文物,那乡村这些呢?”
二、在卫润德还是侨联委员的时候,他负责联系在香港的族人,邀请他们回来。对于那些偷渡者,卫润德提倡对他们“既往不咎”,也正是通过他的努力宗族聚会才得以复办。当时还有两位老人跟他一起,现在那两位都已去世了。
他举了个例子:“我有个兄弟,以前在沥滘出生长大,后来去了台湾,在国民党那大概做了政府机关的一个首脑。那时81年,他想回沥滘参观。当时我就向村委说,台湾那些兄弟回来,你们接不接待?然后我跟我那兄弟说,过去就是过去啦,既往不咎,欢迎回来。”
龙舟是水乡的灵魂,而“沥滘”,从名字上看就是“沥水之地”。每逢端午,大大小小的河涌就成了龙舟竞赛的水道。这一风俗在建国后渐趋消解,终在“破四旧”中被彻底取缔。1982年,卫润德重新操办起龙舟赛事,他与同道一起,号召村委出钱,把龙舟赛重新办成每年一次的盛大活动。
可惜命途多舛,五年前,一位族人在登船时跌入水中,不慎淹死。龙舟活动为此停办许久,期间也有人叫卫润德重操旧业,可是原本那艘龙舟太久没用已经腐坏了,而若是买了新船,又不知道平时该埋在哪里。卫润德跟造船的沟通过几次,但都没有成功,因此也就“不打算折腾”了。
直到今年,有几个族人找上卫润德,打算自己出钱办龙舟,当作“玩玩”。他们一共购置了两艘龙舟,招募了不少“船员”,最终才把这项传统习俗重新带回沥滘。
城市化给沥滘这座古村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从岭南水乡演变为“城中村”的过程中,就像有两股力量在同时作用,一股在把外地人拉向沥滘,一股则把沥滘的卫氏族人往外拉。现在卫氏在村中只占不到四分之一,各经济社的管理层也几乎不见他们的身影。从前的名门望族,“十三代书香”,现在成为了普通的村民、股民。唯一还能让人想起卫氏特殊身份的,大概就只剩下偶有活动的宗亲会,还有矗立在珠江岸边的大宗祠了。
但宗祠也已不再辉煌,宏伟的正门只在清明聚会时打开过一次,之后就再没有打开。大门的地基已经下沉,底下几乎被腐蚀一空。作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宗祠的维修必须上报文物局,由于费用上一直没协调好,维修就搁置到现在,一拖已是三年。从前卫氏宗族有七百亩族田,依靠田租收入举办活动,在土地被收归国有之后,缺少了经济支柱的祠堂如同一个“空壳”,连维修都得依靠临时的捐助。
对卫本立来说,没有失去祠堂已经是足够幸运的事情。早在建国初卫氏大宗祠就“上交国家”,相继被用做收容所、劳改所。随后在“”时期,周围几乎建满了工厂,因为工人和“劳改犯”在村中没有住处,便将祠堂用作宿舍。1959年,国家动员各村修水闸,由于木料短缺,村委从村中数间祠堂里拆了不少木头。后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宗祠很长一段时间被用作仓库,老照片显示,那时的祠堂已是“面目全非”,整个大门被水泥糊住,只能隐隐约约看出三厢的结构。
80年代,“国家”将宗祠的使用权交给粮食局,宗祠就被用作粮站。当时卫本立曾动了收回祠堂的心思,但又害怕遭到政府的批评而不敢开口。直到有一次当地一位领导找到他,想让他代表卫氏宗族主动提出收回大宗祠,他才吃下一颗定心丸。最终90年代,在他多次努力的交涉下,宗祠的管理权终于通过村委会转交到卫氏族人手中。
2004年他们发起了对宗祠的重修,通过广泛动员村里人以及香港和海外的族人,共筹集了50多万。同时粮食局资助了5万,海珠区政府资助了30万,再加上沥滘村委出了50多万,终究凑够了费用。而“卫氏大宗祠管理委员会”这一机构,正是成立于这时。
在中国传统的家族观念中,祠堂的宏伟是宗族兴旺的象征,而宗族的兴旺则是每一个族人的人生价值所在。就这样,一个人与一座建筑的命运交织在一起。世事变迁,不仅写在老人们的脸上,也体现在祠堂历经沧桑的容颜。

三、原本高大宏伟的祠堂,如今已被六七层高的楼房包围,成了在林立高楼中的一处隐蔽之所。经济的发展吸引了大型企业的到来,这些楼房大多被用作仓库,也不时有货车来运输货物。一次货车在倒车时,就不小心撞碎了祠堂一角的砖瓦,后不得不垫付全部维修费用。
城市化的进程为沥滘吸纳了大批的劳动力,也催生了水涨船高的房价。原有的祖屋在利益的驱动下不断搭建,形成密不透风的“握手楼”。本地卫氏族人依靠房租和分红就能过上体面的生活,但他们也被村里人视为是“食利者”。按现代观念来看,卫氏的男人是无法容忍的。如卫本立,一辈子没有做过饭,而许多卫氏的男青年衣食无忧,便失去了上进心,整天待在村子里打牌、打麻将。相比之下,卫氏女性反而玩的比较少、干活干得多。但是对于女人们平时具体做些什么,卫本立便不知道了,他并不关心。
本地人与外地人的矛盾甚至在“旧村改造”临近拐点时更加激化了。本来沥滘不止卫氏一族,但随着其他宗族的大量外迁,他们的祠堂也因不同原因相继被拆,卫氏就成了本地人的象征。外地人纷纷指责本地人为一己私利阻挠改造,这样的争吵在网络论坛和现实生活中早已屡见不鲜了。
现在卫本立心头最牵挂的事就是把族谱修好。原本的族谱毁于“文革”,如今只剩各房支单独的族谱了。大概从几年前开始,他就委托宗亲会去找族人收集家谱和其他材料。没有人付他酬金,他也不需要报酬,他只是希望,趁自己还没老得写不了字之前,把修谱这件任务完成了。
现在的宗亲会还只是个没有身份的组织,在官方的话语体系中,只有“卫氏大宗祠管理委员会”。缺少身份就意味着缺少行动的主体,在卫润德看来,他们无时无刻不想收回大宗祠外其余祠堂的管理权,但又深知所要面临的重重困难。其余的祠堂散落分布在沥滘各处,它们管理权属于各经济社,因此有的出租作仓库、有的作为员工宿舍、有的成了城中村改造规划展览厅、还有的被用作小型图书馆。它们的用途决定在经济社的手里,而经济社早已趋于公司化运作,追求的是股东利益最大化。想要收回这些祠堂,就意味着要让各经济社放弃可观的租金收益,无异于割肉。
谁也不知道,发生在玉溪卫公祠身上的事件会不会重演。玉溪卫公祠是沥滘的“第十三座祠堂”,当时它还没有被挂上文物的牌子,但也是一座有着三百多年历史、具备“三间两进两廊”完整结构的老建筑了。09年时,沥滘村旁一小区正在建设新的楼盘。由于祠堂位于规划中的新楼盘处,开发商一直想把它拆掉,但遭到了卫氏族人的强烈反对。
按照卫本立的说法,村委收了开发商的钱,在整个事件中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卫氏族人找到学者向文物局建议,将玉溪卫公祠列入文物保护单位,认为这样就能受到“国家”的保护。在此过程中,他们害怕祠堂被强拆,于是派人在白天警惕地保护祠堂。可当开发商听到消息的时候,于当晚凌晨时分把祠堂迅速推平。百年的木头不敌推土机的钢铁之躯,卫氏族人一觉醒来发现为时已晚。
卫本立参与了祠堂的抢救工作。他们赶在开发商之前把建筑材料“救”了出来,期望有朝一日借此重建祠堂。最后的协商结果是,开放商承诺给予卫氏族人300万补偿,当作祠堂的重建费。但卫氏族人并不需要赔偿,或者说他们觉得这些赔偿是远远不够的。他们希望开发商帮他们重建祠堂,但开发商只承诺城中村改造完成后再建。现在这些材料都堆放在卫氏大宗祠一侧的小巷,放在一处简易搭起的棚子下面。
不是只有蛮横的资本才是他们畏惧的对象。90年代时,政府希望为当地著名的革命烈士卫国尧修建一所纪念小学,拟选址处包括一所卫氏祠堂和一所外姓祠堂。当时反对的声音不少,但大家觉得毕竟是个“公益事业”,于是方案最后还是付诸实施了。现在卫本立却对此懊悔,他说如果再给他一次机会,他无论如何也会反对到底的。
四、在我们即将离开沥滘村的时候,卫润德的一位朋友知道我们是大学生,便拉着我们说,“你们想一下用一个什么好的标题去发表,登一下广州日报,唤醒大家多一点爱自己的乡土文化!”几乎不给我们打断的机会,他继续说道,“带动他们参与、热爱,吸引他们讨论、引起话题,这样你们的工作才有交代嘛。”他还特地强调,“陈市长现在非常重视的。你们做了这件事,我们街道、文化站,都会对你们很感激的!”
我们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好,也想不到他们能怎么感激,便只好笑着附和,然后跟他一起谴责一下改造工程。这时候他继续说道,“我们这一代还有一些念想,到了下一代呢?你们要想想怎么让80后90后传承下去。”
正当我们想再询问祠堂的过去时,一旁的卫润德却说,“不要讲这些东西了,讲多错多!”他仿佛在自我压抑,但仍自问自答般继续说道,“但这是不是错呢?不是错!”
就这样我们离开了沥滘。关于祠堂的未来,卫润德没有说什么,他觉得那已经不是他们该管的事了。“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我都这么大年纪了,难道要我们搞到死啊?”
此时的卫本立,刚刚收拾好满桌麻将。沥滘村头的码头边,聚集的是跟他一样的老人,在炎热的夏天,河风拂面,比宗祠里要凉快多了。卫本立跟其他朋友打了招呼,就赶着回家吃饭。对于他而言,一天的生活才刚刚开始。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感谢每一位辛勤著写的作者,感谢每一位的分享。

相关资料

- 有价值
- 一般般
- 没价值








24小时热门
推荐阅读


关于我们

APP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