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黑玫瑰与白玫瑰:一边是妻子,一边是情人
一、张兆和:情书里的爱情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沈从文致张兆和的情书
在沈从文写给张兆和的情书中,这是最动人心魄的一个美丽句子。因为这句深婉有风致的情话,我曾相信了爱情的纯美,誓言的忠贞,水会流走云会散去,而所爱是唯一的。

1931年的夏天,在中国公学教书的沈从文,跌入了那场无药可救的暗恋。张吉友家的三小姐张兆和,名门才女,聪慧美丽,演话剧,跳芭蕾,有如一只姣好傲然的“黑凤”,飞入了沈从文多情的相思梦中。沈从文疯狂地给自己的女学生张兆和写了一封又一封情书:“我不知怎么忽然爱上了你!”“你是我的月亮……”情思如月华痴惘,言辞如流水唯美。张兆和对这个腼腆乡土的老师心生不耐烦,终于告到校长胡适那里去了。胡适看了信笑笑说:“沈从文先生固执地爱你!”张兆和回答说:“我固执地不爱他!”
张兆和在日记里抒写了自己的爱情观:“胡先生只知道爱是可贵的,以为只要是诚意的,就应当接受,他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他没有知道如果被爱者不爱这献上爱的人,而光只因他爱的诚挚,就勉强接受了它,这人为的非由两心互应的有恒结合,不单不是幸福的设计,终会酿成更大的麻烦与苦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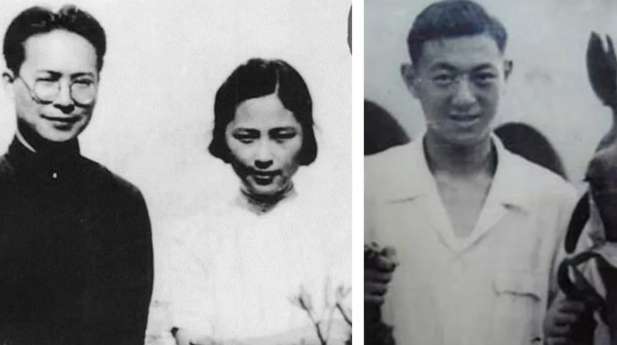
在这场爱情追逐的最初,显然,张兆和是骄傲的,高高在上的,带着名门淑女的矜持与优越感;而沈从文是谦卑的,俯首并仰视的,是一个“乡下人”的自卑的多情。两人的位置处于女神与奴仆的倾斜角度,沈从文的爱充满了一种求之不得梦寐思服的美与哀愁。
“每次见到你,我心里就发生一种哀愁,在感觉上总不免有全部生命奉献而无所取偿的奴性自觉,人格完全失去,自尊也消失无余,明明白白从中得到是一种痛若,却极珍视这痛苦来源。”
“我把你当作我的神。许我在梦里,用嘴吻你的脚,我的自卑处,是觉得一个奴隶蹲到地下用嘴接近你的脚,也近于十分亵渎了你。”
“望到北平高空明蓝的天,使人只想下跪,你给我的影响恰如这天空,距离得那么远,我日里望着,晚上做梦,总梦到生着翅膀,向上飞举。向上飞去,便看到许多星子,都成为你的眼睛了。”
沈从文痴迷的情书一封封不停地写去,一直写出自己的灵魂之美,真情之挚,赤子之心。沈从文的忧伤感染了张兆和,他终于渐渐打动了少女那颗矜持的心,“我虽不能爱他,但他这不顾一切的爱,却深深地感动了我,使我因拒绝他而难过。”
对于一个女子来说,感动即是接受爱的开始。不过,与其说是张兆和因被爱而产生了主动的爱,不如说,她一点点的不自觉地跌入了沈从文温柔的文字陷阱。是情书之美与情书之幻带来的催情作用,让一个少女的情怀开始微醺,讶异爱情的滋味,可能是她从未碰及唇舌的一杯甜酒。她蠢蠢欲饮。
在古典而纯真的年代,文人追求爱情的杀手锏便是情书。如同佐罗用剑与迷人的吻征服了无数贵妇的芳心,文人用他天生擅长的利器——文字,编织美丽的谎言,催开了一座座玫瑰园。文字制造的想象之美,最容易惹出一场爱情的祸。看看我们的祖先,红叶题诗,必定会引出一场以身相许的相思;西厢的张生托红娘夜递几首情书,矜持而犹豫的莺莺小姐就与他“小楼一夜春风”。《爱眉小札》亲啊爱啊浓得化不开;连最讽刺恋爱的鲁迅,写起《两地书》也有几分温柔。难怪乎最骄傲的张兆和,在沈从文谦卑而深情的情书攻势下,终于投下了她感动的一瞥。
1933年的初夏,沈从文在青岛大学一隅的海边捡起一枚螺蚌,轻轻拭去金色的细砂,把它装入信封,寄给了千里之外的爱人(螺蚌有女性生殖器官的隐喻意义):“我不仅爱你的灵魂,而且要你的肉体。”这只拾来的螺蚌“无意中寄到南方时所得的结果”,是“一种幸福的婚姻”。
那年暑假,阳光炽烈而清白,苏州寿宁巷的骄阳下,千里迢迢赶来见三妹的乡下人沈从文,脑门上冒着晶莹的汗水,脸上写着赤诚,不安,又有幸福将至的兴奋。一向拒人千里之外的三妹,终于回信给他,叫他暑假来她苏州的家。这是一个柳暗花明的答复,幸福此刻就在扣响门扉的那一端。但等门打开,站着的是二姐允和,三妹兆和还是回避了他。这个赤诚的乡下人惴惴地回去了。幸好,热心人二姐给他拍来了一语双关的电报:“允。”而不放心的三妹又补拍了一封:“乡下人喝杯甜酒吧。”这是*史上第一封白话文电报,也是沈从文的爱情福音。
1933年9月,沈从文和张兆和在北京结婚。沈从文拒绝了岳父张吉友的钱财馈赠,新房里几乎家徒四壁,除了梁思成、林徽因夫妇送的两床百子图床单。院子里有一棵槐树、一棵枣树,沈从文把他的家称为“一槐一枣庐”。

从此,张兆和成了沈从文生命里亲爱的“三三”。沈从文是个居住在纯美世界里的有情人,他以对妻子之爱,创作了《龙朱》、《月下小景》等如梦如幻的化境小说。他们的两个儿子,分别如他的小说人物取名为龙朱与虎雏。张兆和则是他小说里黑而俊的“黑凤”。
二、高青子:幻想里的“偶然”
“我想,那是一个庇护在爱神与美神羽翼下的家。沈从文为人忠实纯洁,又少与世结交,除了沉醉于小说世界,收集坛坛罐罐花花朵朵,他对妻子的爱,如月之皎皎,纵使渐渐归于平淡,却始终至深而唯一。张兆和融为了沈氏温柔世界里静美生存的一员,直至沈去世。”

后来发现,这是我的一种误读。至少是对沈氏情感世界的认知狭隘而造成的片面化误读。一个朋友指出一个事实:沈从文的生命中,隐约地划过好几次“偶然”的星子,并分明有过一段闪亮天际的婚外恋情!
忙翻阅沈从文记录“偶然”的那篇《水云:我怎么创造了故事,故事怎么创造了我》,惊讶地走进了沈氏纷繁复杂的情感世界:他在情感与理智之间的挣扎,他对婚姻的审美疲劳与他的“婚外情感发炎史”。
情书里的爱情与现实里的婚姻,毕竟有着天上与人间的落差。在情书与恋爱的罗曼史里,“女子是一个诗人想象的上帝”。张兆和在婚前,是在天上的,需要沈从文做梦向上飞才可以抵达;在婚后,张兆和却成了堕落到凡尘掌管柴米油盐的主妇。

早年顽劣高傲好扮男装的张兆和,自从跟随了沈从文,越发地朴素而家常起来,她曾写信给沈从文:“不许你逼我穿高跟鞋烫头发了,不许你因怕我把一双手弄粗糙为理由而不叫我洗东西做事了,吃的东西无所谓好坏,穿的用的无所谓讲究不讲究,能够活下去已是造化。”——张家小姐的妇德真是了得,当沈从文一味沉醉在创作中连生活都不能自理时,“家务全靠妈妈打理”(沈虎雏语)。从当初的被爱的荣耀到进入妻子角色后的情感反哺,张兆和步入了每个女人那样的嫁夫随夫的宿命。
而在惯于做梦耽于幻想的沈从文这里,却是另一种落差。在得到爱情之前,他把张兆和奉为女神,圣洁美丽,望之叹息;在得到爱情后,当这个女神实实在在地来到他的生活中,为他生子、操持家务,他反而发现女神的光环褪去了,先前因距离产生的“惊讶”和“美”也逐渐消失。
沈从文的人生,始终是需要审美的,他的一生,是用美来装饰理想的一生。而婚姻的种种现实,往往是与审美相悖的。1936年,在他们结婚3年后,沈从文创作了小说《主妇》,分别剖析了男人与女人在婚姻中的不同心理:“作主妇的始终保留着那幸福的幻影,并从其他方式上去证明它。”而对于男人,“家庭生活并不能完全中和与调整我的生命,我需要一点传奇,创造一点纯粹的诗,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
因此每天大清早,在“一槐一枣”掩映下的院落,细碎阳光洒在红木方桌上的一叠白纸,沈从文一面觉着一种“闷热中的寂寞”,将他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一面用身边新妇作范本,取得性格上的素朴式样,于是有了《边城》与翠翠。

刘洪涛说:“《边城》是沈从文在现实中受到婚外感情引诱而逃避的结果。”
沈从文也自述:“这是一个胆小而知足且善逃避现实者最大的成就。”除了一种湘西理想的构筑即社会意义上的逃避,沈从文还在逃避谁?——“在这时候,情感抬了头,一群‘偶然’听其自由侵入我生命中。”“岁暮年末,偶然中之某一个,重新有机会给了我一点更离奇的印象。”
在写《边城》之前与之后,已然有一个“偶然”的星子萦绕在沈从文的情感天空,让他陷入一种幻想。甚至可以揣摩,《边城》里那个望着黄昏中的汩汩长河,怀着心事叹息的女孩,她之所以被取名为 “翠翠”,是不是也与沈从文默想中的这个 “偶然”名字相应——高青子。青者,翠也。
沈从文与高青子的初遇,是在他大名鼎鼎的凤凰同乡熊希龄家的客厅。“主人不曾出来,从客厅一角却出来个‘偶然’。问问才知是这人家的家庭教师。”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感谢每一位辛勤著写的作者,感谢每一位的分享。

相关资料

- 有价值
- 一般般
- 没价值








24小时热门
推荐阅读


关于我们

APP下载




























{{item.time}} {{item.replyListShow ? '收起' : '展开'}}评论 {{curReplyId == item.id ? '取消回复' : '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