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化—四川方言—“川语”能否上台面?(四川方言趣谈三)
四川人这个居民群体,为何普遍保持一种“嗜好语言”的风俗习惯呢?“川语”拿出去交流,能否上得了台面?
● “川语”的生存环境
要揭开四川人天生“嗜好语言”之谜,要对“川语”的地位和发展前景作出评价,不能不从四川语言的生存环境说起。
据研究,近代以来,国外有人把正统精神分析学派关于人格结构与意识的关系进行归纳,断定人在一岁时,正处于口欲期,口欲分为两种:“掺合性口欲”和“攻击性口欲”。“掺合性口欲”为日后的同化、占有、信仰型性格的基础;“攻击性口欲”,则为日后嘲笑讥讽,好辩论型性格的基础。不知道四川人自古以来这么嗜好语言,好持短长的性格特征,是否与他们先民在口欲发育期具有某种“攻击性口欲”的遗传基因有关。
先天说不清楚,自然人文生存环境对四川人性格的后天影响,则是衙门口的狮子——明摆着的。
人类在初民时代,由于抽象思维不强,缺乏今人的概括能力,以致在说话时,往往只能通过对客体外观的感知程度来描绘事物。大体说来,旷野中生活惯了的人,因为周围事物清晰可见,致使人们在描绘其外部特征时,往往多使用形容词,多借用比喻来表达。古代文献上常言四裔部落居民“语言多比喻”,就是这个道理。《汉书》就记载,蜀郡青衣道(今名山县)的居民,“人皆被发,左衽,言语多好譬类。”证明四川自来就是以善用比喻语言而著称的。
经常在丛林中生活的人,由于观察事物不如旷野中那么丰富清晰,很多事物的判断要凭耳朵所听到的声音来弥补。所以,这里的居民多使用形声词。如在岷山、大巴山、邛崃山脉林区土著常用语中,“我听见”一词的使用频率,远比“我看见”为高。今天四川人在与人谈话时,经常不断发出“啊呀!”或“呀!呀!”之类惊叹语言,这正是受丛林初民谈话遗风影响的结果。须知,在丛林部落间彼此对话,不经常以这类惊叹语回应,对方会以为你没听见,或是睡着了,而那是很不礼貌的事。
四川人说话爱发惊叹语的现象,早在宋代即引起陆游的注意。他在《老学庵笔记》中,就曾经嘲笑当时的蜀人,凡遇到值得赞美的事物,总爱说:“呜呼!”凡遇鄙陋的人,则说:“噫嘻!”流沙河考证说,古时的“呜呼!”就是今天四川人常说的“哦哟!”如说“哦哟,好啊!”古时的“噫嘻!”就是今天四川人常说的“哦嚯!”如说“哦嚯,死了!”
长期生活在山谷丛林中的巴蜀人,与邻近的荆楚之民一样,很早以前就以先祖为“鬼”为“巫”,想象力十分丰富。故当他们面对高不可攀的山崖,深不见底的幽谷,阴森恐怖的密林,遮天蔽日的迷雾感到困惑之时,总会产生种种奇特的幻想、无穷无尽的揣测。因此,他们的神经十分敏感,思维多有灵性,故能在语言文学上,神思诡谲而文采斑斓,创造出无数诡异奇幻而又绮丽动人的文学艺术作品。从汉赋作家司马相如、扬雄、王褒、李尤,以陈子昂、李白、花间派词人,再到苏轼、杨升庵、李调元,以辞赋和诗词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四川文学殿堂,无不是用华丽的辞藻语言构建而成的。
如果说多样化的生存环境,对丰富四川人的语言天赋、灵感、创造能力,以及表达方式、习惯产生的影响,足以润滑四川人的舌头,培育他们的语言嗜好的话;那么,生活容易,节奏舒缓,也使他们具有较多的时间空间来操练嘴上功夫,显示说话的能力。因此,对于生性豁达的四川人来说,说话已不仅是说出来供外人听,而且,也是为了供自己说着玩。正如《成都人》一书所描绘的那样:成都人“把话语在舌头上颠来颠去地品味、欣赏、展示。犹如绿茵场上的好手,把一颗皮球在脚尖头顶颠来颠去颠出万千花样来一般。他们爱热闹爱交流,爱说话爱逗乐。哪怕是骂人吧,其实更主要的也是为了取笑逗乐,外带展示自己的口才风采。
● 一道尚待加工的“川菜”
四川人嗜好语言,语言生动形象,很有特点,但它却像一道还未加工烹调的“川菜”一样,如不经过精心的加工制作,一时还上不得文学艺术的台面。要拿得出在全国的乃至世界上风味独播、盛誉独享的“川菜”,造就出在全国叫得响的有影响的“川派”大腕明星来,还得正视和突破四川人文生态环境对语言功力的深度和广度的限制。
偏处西南一隅的四川,除了封闭的自然地理环境限制了人们的眼界外,在人文因素方面,也有两个因素对四川语言造成了影响:
一是历代政治文化对语言的影响。自古以来,四川远离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缺乏与全国范围的沟通与交流,在总体上限制四川人的视野范围和思维的深度,即使历史上有过几度偏安王朝立足四川,曾经把四川文化提升到“国家”规模的水平,但地也只是“小朝廷”的经营和过眼即逝的烟云,因此,这些都不能不限制语言表达功力的发挥。
二是清初移民文化对语言的影响。今天四川人中流行的名为“摆龙门阵”(相当于聊天、侃大山)、“摆闲条”、“冲壳子”(吹牛)、“涮坛子”(开玩笑)之类的谈话方式,就是清初“湖广填四川”那个飘泊不定的移民时代的产物。来自各地的创业者,往往通过当时唯一可行的简单的表达形式——语言,用包含各种调笑的谈话,来缓解面临的困难,协调彼此的紧张关系,并抒发自己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在这种社会背景和谈话方式中发育起来的语言,必然跳不出平民化、市井化和粗俗化的轨迹。
正因如此,四川人的语言表达,虽然不乏生动活泼富有创造性,但同时又存在着涉及层面不宽,内涵欠深,气度不大,话题大多跳不出世俗琐碎的圈子,难与时代精神相碰撞等不足。如果拿它们到外部世界一比较、交流,难免不在思想内容、文化品们和审美价值等方面,流露出粗俗浅陋的缺陷。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比起字正腔圆、干脆利落的北方话,四川人说话欠力度;比起婉转细语、舒心爽骨的江南话,四川人说话少深度;比起拖声拉调、华洋混讲的广东话,四川人说话缺广度。既然在力度深度广度三方面不足与人抗衡,四川人说话则只好在台面下,弯过去绕过来,打点比譬,展点言子,耍点嘴皮子,说点俏皮话,显点小聪明,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成都人》一书对四川人在语言上表达上不得台面的现象,举了一个典型的例子:“要说成都人能说是能说,就是上不得台面,真要遇上正经八百的场面就惨了。就是那些伶牙俐齿的妹仔,只要是放个话筒到她嘴边,舌头就抖不转了:‘这个吗,等于是……啷个说喃,等于是这样子的……嘎……唔,对的,就是等于是……’态度比平时和气十倍,脸笑得稀烂,眼睛成了豌豆角,但就是说了半天,还是‘等于’不出个名堂,叫人不知所云。
在一个学术会议上,我们也同样目睹过这样的场景:一位日本教授在会上发言,有两个中文翻译轮流口译。一个来自北京,一个来自成都。但见北京翻译口译起来,气贯长虹,生动流畅,令人佩服;而轮到成都翻译上阵,译得来节节巴巴,水平高低尚且不说,就是那满口的“等于是“、“就是说”,直听得与会者心烦,更让四川本地人汗颜。
针对四川人经常说一些类似于“等于是”这类让外人不懂,“上不得台面”的方言,有人戏作诗曰:“近年流行‘等于是’,同时爱说‘晓不得’。更有费解‘不存在’,听来让人如猜谜。”“流行方言好尴尬,心中意思难表达,劝君从此将它弃,努力学好普通话。”
在成都颇有影响的艺人李伯清,以“散打评书”引起轰动,他的一些讽刺挖苦小市民虚情假意的表演段子,如《假打》、《世态百象》等,家喻户晓,录音录像带流行于四川城乡的大街小巷,深受许多喜欢市井文学的人的好评。但是,当把他请进中央电视台一亮相,他可就“惨”了:那川味椒盐普通话,说得来费劲蹩脚,让外省人听起来不是滋味,四川人听得来也是浑身直起鸡皮疙瘩。平时舞台上那口似悬河的谈吐,潇洒自如的风姿,川人特有的机智风趣,都不知跑到哪里去了。与同一栏目中北方评书艺人袁阔成、刘兰芳的表演艺术相比较,差距是那样的明显,难怪后来他的“散打评书”在中央电视台草草收场,失去踪影,最后只落得退居四川,在盆地内“孤芳自赏”。
● 走向中国要说“普通话”
当然,这绝不是说以语言类为主的文学艺术领域,四川人不能登大雅之堂,只配在台面下活动。应该承认,要把“四川话”这一特别的“原料”加工成一道上得了台面,能让全国观众都能接受的艺术表现形式,是需要花费比直接北方话更多的功夫,但绝非没有成功的先例。从电影《抓壮丁》和电视《死水微澜》(川语版),到《哈儿师长》、《山城棒棒军》等,都以其独具魅力的川腔川味征服了广大观众,成为脍炙人口的之作。由这些作品所显示的四川语言的魅力和意趣,是其他地方语言难以匹敌的,表明经过加工制作后的四川语言,是同样上得台面,可以而且必然能够从巴蜀走向全国的。
在最近举办的历时半年的“川航杯”巴蜀笑星擂台赛上,众多笑星竞相登场献艺,再一次展示了四川人的语言功夫。他们通过一个个精彩的节目,把四川人对于笑与喜的领悟与表现,展示得淋漓尽致,受到了巴蜀乃至全国部分电视观众的喜爱和好评。在擂台赛的颁奖晚会上,北方知名笑星应邀到场,与代表南方的巴蜀笑星同台竞技,联袂举办了一台南北笑星的搞笑演出,更把这一次擂台赛推向高潮。从这次活动取得的巨大成功中,再一次显示了有着“嗜好语言”传统的四川人和重庆人,最懂得欣赏喜和笑的语言表演艺术。人们从近距离的观察比较中,感受到南北语言艺术上的不同风格特点,同时也发现四川笑星在语言艺术上的差距和不足。相信这种交流与沟通,有助于四川笑星群体尽快登上台面,走向全国。
从文化学的意义上讲,“川语”公是地域文化的产物,四川人要实现“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远大目标,必须讲“普通话”,即必须走出盆地,与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相沟通。这不仅因为,四川方言的地域特点,决定其表达不够规范,“上不得台面”,许多字词连字典上都查不到,不能不妨碍与外界的交流;更重要的是,作为地域文化产物的“川语“,是深深地植根于四川盆地和巴蜀地方文化之中的,如果不挖掘出一条沟通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井”,是很难有所作为的。
有人说:“愈是民族的就愈是世界的”,这话也对也不对。如果不用“世界的”眼光来衡量“民族的”,“民族的”永远不能世界化,只能是与世界潮流不相融的偏狭的东西。有们年轻学者说得好:“乡土爱缺乏大视野,就会患文化自闭症,就会成为一枝顾影自怜的老水仙!”只有用“世界的”眼光来衡量“民族的”,审视其是否独特地提出对本民族以外的人类有价值的东西,这样的“民族的”才可能成其为“世界性”。
同理,要使四川的语言这一特殊的“原料”,能够生产出上得台面的,成为通向全国乃至世界的文学艺术作品,造就出具有全国影响的大腕级的“文艺川军”群体,有一个自身突破地域文化限制,从文化素养上吸取世界文化精华,具备“世界的”视野视界的问题。这方面,四川现代作家、前辈文艺大师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范本。
在现代文学史上,曾经涌现出一个令四川人自豪的“文豪群体现象”,以郭沫若、巴金、李劼人、沙汀、艾芜、阳翰笙、何其芳、马识途等为代表的一批四川籍作家,以他们出类拔萃的丰硕成果,留下了厚重的笔触,书写了光辉的一面。他们经常自诩为“我是四川人”,他们从巴蜀文化(包括四川语言)这座丰富的矿藏中吸取营养,创作出了傲立于全国乃至世界文学之林的作品。与其把他们的创作视为四川特定的区域文化影响下的产品,不如说是四川的区域文化与外省文化相碰撞的产品。站在东西方文化对话的层面上看,这些四川作家的创作,又是东西方文化冲撞与交融的产物。
我们之的以能够从整体上冲出盆地,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不仅值得文学艺术界人士,而且包括各行各业在内的所有的四川人学习和反思。青年学者李明泉《剪不断的文化脐带》一文从文化思维的角度作的考察,给我们以启示。他指出:“从人生经历来看,郭沫若、巴金、李劼人等人都处在新旧时代的断裂带,青年时期出国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系统地受过异域文化的熏陶。他们都从事过翻译工作。这样,使得他们一旦重归帮里,就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汇中,在异域文化的参照系里,比常人要多一只眼,多一份心,也多一种情地看待、热爱和表现中华民族及四川生活的现实与历史,其透视着力点、视界视域就更为精深和博大。”
由此看来,只有把巴蜀文化与异质文化自觉熔铸的人,才可能获得比常人“多一只眼”、“多一份心”、“多一种情”地审视和表现生活周围的历史与现实,才可能开掘一口既属自己而又与全民族、全世界的大河相畅通的“文化井”,从而缩短“川语”与“普通话”的差距,实现从“民族的”走向“世界的”的飞跃。
立志冲出盆地,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四川人,让我们以前辈大师为榜样,继承他们的文化传统,展开双臂,接受八面来风,勇敢地在同异质文化的交流碰撞中,超越自我,实现自己的理想吧!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感谢每一位辛勤著写的作者,感谢每一位的分享。

相关资料

- 有价值
- 一般般
- 没价值








24小时热门
推荐阅读
知识互答
关于我们

APP下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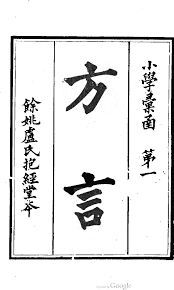











{{item.time}} {{item.replyListShow ? '收起' : '展开'}}评论 {{curReplyId == item.id ? '取消回复' : '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