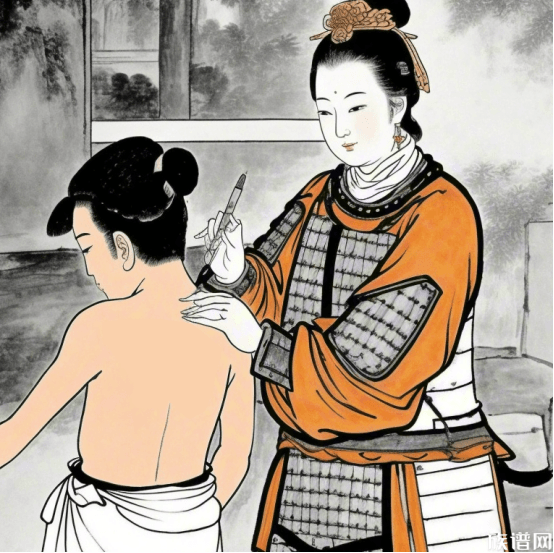东北文化—历史溯源—“流人”,创造了黑土地时代的文明
古老的黑土地上,历经多少历史的风霜雨雪、沧海桑田!自古物华天宝的黑龙江,地杰人灵。也正因为有了人,才有了白山黑水的灵气。回望历史,人们总是会想到那些边关战事、朝代更迭,记住那些轰轰烈烈的历史大事,有谁会忆起那些屈辱的流人给这块土地带来丰厚的滋养。如今,中华版图上的“天鹅”已不再原始和荒凉,浩浩历史长河,凄凄流人文化!历史应该记住流人曾给这块土地播下的文明种子。
在数百年前的满清王朝,“流放宁古塔”是人们对黑土地最多的记忆。其实,宁古塔没有塔,宁古塔三个字是满语的音译,意为“六个”(“宁古”为“六”,“塔”为“个”),据说很早的时候曾有兄弟六人在这里住过,而这六个人还与后来的清室攀得上远亲。
三百多年前,冰冷遥远的宁古塔是流人的土地,也是他们的第二故乡。当他们对着“流放宁古塔”圣旨谢恩之后,他们带着夹板,带着不明不白的屈辱,经过几千里路途的艰辛和苦楚,走上了流人必经之地大石桥,站在大石桥上之时,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们苦难的流放,给这片神奇的黑土地带来的新鲜血液,带来的先进,带来的创造!还有黑土地的坦坦荡荡!“流人”,创造了黑土地时代文明,创造了黑土地的博大精神。今天黑龙江人的豪爽、好客、重友情、讲义气,我们不能不说是流人们精神的张扬。
吴门流人吴兆骞
从顺治年间开始,宁古塔成了清廷流放人员的接收地。有许许多多的流人来到荒凉凄苦的北大荒,有的是官吏、文人雅士,有的是艺匠、官人,有的是战俘,也有平民百姓千里赴北疆。不同的人,不同的遭遇,不同的罪名,走上同一块土地。他们在这塞北寒山饮凄风苦雨、茹荒野寂寥,可谓“古戍黄沙迷断砖,羊裘坐冷千山雪”。他们当中有抗清名将郑成功之父郑芝龙;文人金圣叹家属;著名诗人吴兆骞;思想家吕留良家属等等。在悲惨的境遇中勉强生存的同时,他们也为边疆的经济建设、文化、教育、艺术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惊才绝艳”的江南名士吴兆骞应该是一位杰出的代表,他出身书香门第与贵贾之家,他“少颖悟,有奇才”,“七岁参玄文,十岁赋京都”,“十三学经史”,九岁时就写有数千言的《胆赋》。顺治十四年,兆骞参加了南闻乡试,考中举人,但不久在震惊朝野的江南科场案中“为仇家所诬陷”,由于“一纸谤书”的诬陷而衔冤入狱,虽然最后“审无情弊”,但仍于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判处遣戍宁古塔。初时囊空如洗,生活艰难,后其妻出塞来到戍所,“携来二、三婢仆,并小有资斧”,生活稍有好转,此后以授徒为生,先教流人子弟,后来当地少数民族子弟也有从学者。康熙四年夏,他与张绪彦、姚其章、钱威及钱虞仲、方叔、丹季三兄弟结“七子之会”,是为黑龙江第一个诗社。康熙十三年秋,时黑龙江将军巴海聘请吴兆骞为书记兼家庭教师。后经友人搭救,于康熙二十年七月还乡。兆骞著述颇多,但大都失传,今传《秋茹集》、《归来草堂足族》。他的诗典雅华丽,出塞后因生活在民间,使诗作更具有了新的意境和现实主义的文风。如“冕戌自关军国计,改将筋力怨长征”(《可汗河晓望》)、“幕府只今勒远戌,敢将离思问重逢”(《送姚琢之戍冗喇》),表明了对抗俄斗争的积极支持。
李兼汝是靠同样在流放的杨越的帮助,偷偷逃走踏上回乡之路的。他被流放后,一直靠一起流放的朋友杨越照顾他,后来他年老体衰,实在想离开这个地方,杨越便想了一个办法,让他躲在一个大瓮里由牛车拉出去,挥泪作别,自己再回来继续流放。这件事在流人中悄悄传开来了,杨越成为无私的流人精神的象征。苦难让友情升华,今天黑龙江人真挚、豪爽分明也接受着流放者遗传。
在这些流人中,吴兆骞和李兼汝是比较幸运的,在他们人生的最后几个春秋离开了宁古塔。更多的人则是留在了黑土地上,成为黑土地文化的先驱。
离开熟悉的江南,来到冰冷的北国,流人的生活是艰难的。为了生命的延续,抱着仅存的希望,他们寻找自己的生活。他们在黑土地贫瘠的文化土壤里找到了自己生命的空间。流人们比较常见的是选择教书。例如洪皓曾在晒干的桦树皮上默写出《四书》,教村人子弟,张邵甚至在流放地开讲《大易》,“听者毕集”,函可作为一位佛学家当然就利用一切机会传播佛法;其次是教耕作和商贾,例如杨越就曾花不少力气在流放地传播南方的农耕技术,教当地人用“破木为屋”来代替原来的“掘地为屋”,又让流人随身带的物品与当地土著交换渔牧产品,培养了初步的市场意识,同时又进行文化教育,几乎是全方位地推动这块土地走向了文明。流民的涌入改变了当地以渔猎为生的原始生活方式,教他们种植稷、麦、粟、烟叶,采集人参和蜂蜜,使农业耕作得到发展。正是为了自己的生存,不知不觉中传播了中原文化,使南北方人民的文化交流得以沟通。
文化素养更高一点的流人则把黑龙江这一在以往史册文典中很少涉及的角落作为自己进行文化考察的对象,并把考察结果以多种方式留诸文字,至今仍为一切进行地域文化研究的专家们所宝爱。例如方拱乾所著《宁古塔志》、吴振臣所著《宁古塔纪略》、张缙彦所著《宁古塔山水记》、杨宾所著《柳边纪略》、英和所著《龙沙物产咏》、《龙江纪事》等等便是最好的例子,这些著作(有的是诗集)具有极高的历史学、地理学、风俗学、物产学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是足可永垂史册的。
在这整个过程中,有几个代代流放的南方家族给黑土地所起的文化作用特别大,例如浙江的吕留良家庭、安徽的方拱乾、方孝标家族以及浙江的杨越、杨宾父子等。近代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在民国初年曾说到因遭文字狱而世代流放黑龙江的吕留良(即吕用晦)家族的贡献:吕氏“后裔多以塾师、医药、商贩为业。土人称之曰老吕家,虽为台隶,求师者必于吕氏,诸犯官遣戍者,必履其庭,故土人不敢轻,其后裔亦未尝自屈也。
到宁古塔流放的人创造了一个奇迹,不少被流放的清朝官员与反清义士结成了好朋友,甚至到了生死莫逆的地步。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利益冲突都消解在北国的风雪中,消解在对人生价值的重新确认里。这种消解实质上是一种融合。共同的境遇是不同的人群之间相互包容,形成了今天黑龙江文化的多元性中的统一性。
“宁古塔”三个字,承载了三百多年的历史,而流人途径的“大石桥”目睹了世事沧桑。她听到过流人的浅酌低唱和痛苦呻吟,也看到过长空飞雁和肥鱼硕米。她是流人断魂的墓志,也是流人思归的梦乡。
“人自东流,水自西流。古人谁似我淹留?”这是流人才女徐灿内心的呼喊!如果,时空可以穿越,她会知道,她们的“留”,形成了今天的“流人文化”!
我们承认历史,承认流人的苦难,但,苦难的结果未必永远是苦难,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流人也创造了文明,在一个原本荒凉的土地上创造了一个迅速开化的状态。流放的苦难中显现人性、创建文明,本源于他们内心的高贵。凭着这种高贵,他们可以在生死存亡线的边缘上吟诗作赋,可以用自己的一点温暖去化开别人心头的冰雪,继而,可以用屈辱之身去点燃文明的火种。他们为了文化和文明,可以不顾物欲利益,不顾功利得失,义无反顾。一个家族世世代代流放下去,对这个家族来说是莫大的悲哀,但他们对黑龙江的开发事业却进行了一代接一代的连续性攻坚。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感谢每一位辛勤著写的作者,感谢每一位的分享。

相关资料

- 有价值
- 一般般
- 没价值








推荐阅读
关于我们

APP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