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陇文化—西夏民族宗教—西夏建国以后藏传佛教的宏传(一)
西夏佛教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极强的实践性和高度的包容性。这种佛教并不重视其遵循何种流派,奉行何种教义,而是强调通过直观的可以操作的宗教仪式上信徒取得如此行动之后的精神安慰感,西夏大规模的译经与刻经活动就是如此,并非要建立自己的佛教体系。西夏佛教同时将汉地佛教和藏传佛教兼收并蓄地融和在一起,极为侧重有关实践的内容,藏传佛教中噶举派的教法具有明显的实践色彩,正好迎合了西夏佛教重仪轨重实践轻理论的特点,使其在西夏朝野得以迅的速的传播。
整个12世纪,西夏没有和吐蕃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近一百年的和平时期为西夏和吐蕃的文化交往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社会环境,而河湟吐蕃时期佛教的兴盛则为后期藏传佛教在西夏的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我们在讨论吐蕃文化对西夏的影响时,应该充分考虑河湟吐蕃对西夏的影响。藏文文献记载吐蕃佛教在西夏建国以前很长时间就已经传入迁徙至内地西北的党项人中间,笔者以为其年代最晚应该早于大师贡巴饶赛(952-1035年),因为大师曾向西夏上师学法。至西夏建国初期,藏传佛教似乎已经盛传开来。事实上,西夏与吐蕃的关系实际上比人们想像的还密切。《宋史?夏国传》记:(德明之子)元昊“晓浮图学,通蕃、汉文字”。在他新制西夏文字以前,所谓“蕃字”就是指的藏文,因此元昊早年已和藏传佛教发生关系,应该是可以肯定的。西夏境内有很多的吐蕃人,他们主要使用藏语,这是藏传风格佛教艺术在西夏广为流传的因素之一,在吐蕃撤出河西敦煌和于阗一线后,藏语文直到10世纪仍被作为官方语言而普遍使用着,以致于出家也要经过层层考试才能剃度为僧人;西夏人在吐蕃人聚居的河西立碑时不用西夏文而用藏文,可见此地使用藏文已经有不短的时间了。今存敦煌写本《嵬名王传》,则是西夏民间用藏文字母代替西夏拼音写成。
此外,藏语文在西夏境内,还是诵读佛经的必备文字之一,如乾祐二十年的大法会“念佛诵咒,读西番、番、汉藏经”,将藏语经文(西番)放在首位,可见藏语在西夏佛教活动中的地位。克恰诺夫认为,西夏国内佛教徒学习藏语文是强制性的。他还以法典为例,说明藏语的重要性。据统计,要求用藏语诵读的佛经有:《文殊室利名经》、《毗奈耶决定伏波离所问经》、《大方光佛华严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一切恶道消除佛顶尊胜陀尼经》、《无垢净光明摩訶陀罗尼经》和《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多经》等。综上所述,西夏建国以后藏传佛教的流行实际上是党项人的佛教与吐蕃前宏期与后期交替时期佛教关系的继续。因此,我们在分析包括黑水城在内的西夏藏式风格作品时,并不能将这些作品的出现年代严格限定在噶玛噶举和萨迦派僧人与西夏朝廷发生联系之后,而应该考虑党项人和吐蕃的关系,西夏早期、中期和河湟吐蕃佛教的关系。假如没有两者之间地域、民族与宗教之间绵长深厚的历史联系,很难设想10世纪前后后宏期在吐蕃复兴,11世纪后宏期初年复由阿里等地进入卫藏的修行上乐金刚金刚亥母本尊坛城的密法几乎同时能够在西夏广大区域流行。
艺术史家在讨论由西夏使夏的僧人上师时,一致将一世噶玛巴都松庆巴的弟子藏巴敦库瓦入藏作为藏传佛教绘画进入西夏之始,并以此作为西夏传风格绘画断代的依据,从而将出现修习上乐金刚根本续双身像的西夏绘画断在1189年都松钦巴的弟子藏巴敦库瓦赴西夏之后,这种断代无疑是错误的,还会产生一些断代上的矛盾。例如出自贺兰县宏佛塔——一种唐宋以来流行的密檐式砖塔而不是塔——的上乐金刚像,其建塔的年代有可能早至元昊时期,此塔没有重新装藏的迹象,我们很难将他们断代在藏巴敦库瓦入夏之后,即1198年以后。所以,与藏传佛教在西夏传播的历史进程相对应,西夏故地佛塔所出藏传绘画作品表明,早在昊时代这此作品已经存在,至少在仁宗(1139-1193年)初期,藏传绘画已经盛传开来。确凿的文献表明,在噶举派僧人到来之前,当时有来自印度、克什米尔和的僧人久居西夏从事译经事业。例如,明正统十二年(1447年)重刊的汉藏合壁偈子,这份偈子原是仁宗朝从梵文原本译为西夏文、汉文和藏文的,明刊本《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vphags pa shes rab kyi pha rol tu phyin pa yon tan rin po che bsdud pa tshig su bcad pa)保留了一篇明代的序言和一篇原有的西夏题记(仅用汉文),其中提到六个人名,其中有梵文译者遏啊难捺吃哩底、上师拶也阿难捺、主校波罗显胜。据范德康考证,遏啊难捺吃哩底梵文为ānadakirti,还原为藏文为kun-dgav-grags,断定他也是一位吐蕃僧人。拶也阿难捺的名字出现在众多的藏文和西夏文的佛经跋页中,据考他是来自克什米尔的上师。作为译经职位最高的上师,按照西夏僧官制度,应为,所以史金波先生认为波罗显胜是西夏僧人。这些僧人的活动年代大多都在仁宗初年。其时,噶玛举和西夏的联系还没有见诸记载。
我们从西夏大藏经所刊刻的木刻画也可以印证如上记载。西夏文佛经译自汉文的经典一般时代较早,所译藏文经典的时代多在后期。现在黑水城出土或者其他博物馆所藏的带有绘画风格的版画常常被认为是出自西夏文译自藏文的经典、联系到西夏和当时的教派联系的历史事实,常常将这些作品的断代定得较晚,而事实并非如此。带有藏式风格的绘画不仅出现在西夏文佛经中,而且也出现在汉文佛经中。笔者检出西夏雕印的汉文带有波罗卫藏风格的版画最早的作品出自正德十五年(1141年)《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经首版画佛像。其后有天盛十九年(1167年),仁宗仁孝印施流文《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其中的木刻牌插带有典型的卫藏波罗风格,般若佛母的背光式样与扎唐寺壁画大背光及柏兹克里特石窟同期的背光式样相同,更为突出的是环绕主尊的菩萨的头饰与扎唐寺以及后来的夏鲁寺、敦煌第456窟等的菩萨头饰完全一致,画面众菩萨以七分面朝向主尊的构图方式与扎唐寺以及第465窟窟顶壁画大致相同。这件作品的存在本身说明在1189年噶举僧人使夏以前的1167年就有了藏传绘画的雕版印画,其传入西夏的年代应该更早。现藏印度博物馆的黑水城出土西夏文刻经版画残片与此经应该是同时代的作品。又如西夏乾祐二十年(1189年),仁宗印施西夏文《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其时作大法会凡十昼夜,敬请与会的众国师据说都是高僧。在这部汉藏风格合壁的经前插图中,风格被置于右侧卷首最为尊贵的地位。作品中主尊的身相,佛龛宫殿的样式,两侧的立兽以及上面提到的菩萨三角形头饰都与同时期的唐卡作品相同,但是构图方式更像扎唐寺壁画,实际上反映的是汉地中亚的风格。上述木刻作品与1229年至1332年刊刻的《碛沙藏》版中的带的风格的插图在人物造像和母题细节上截然不同,例如,后者作为主尊的佛像已经没有了黑水城版画中与唐卡造像完全相同的粗短脖颈,菩萨三角形头饰倾向于圆形等等,此外,刀法趋于细腻,线条更加细密、流畅和圆润。这些图像都出现在1302年杭州刻印的元《碛沙藏》中,说明当时汉地所绘有关的藏式风格的作品造像特征已经发生了变化。以上的木刻版画都有比较明确的纪年,这就是为本书论述的黑水城唐卡和西夏故地佛塔出土的西夏藏传绘画提供了一个相对的时间坐标。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感谢每一位辛勤著写的作者,感谢每一位的分享。

相关资料

- 有价值
- 一般般
- 没价值








24小时热门
推荐阅读
知识互答
关于我们

APP下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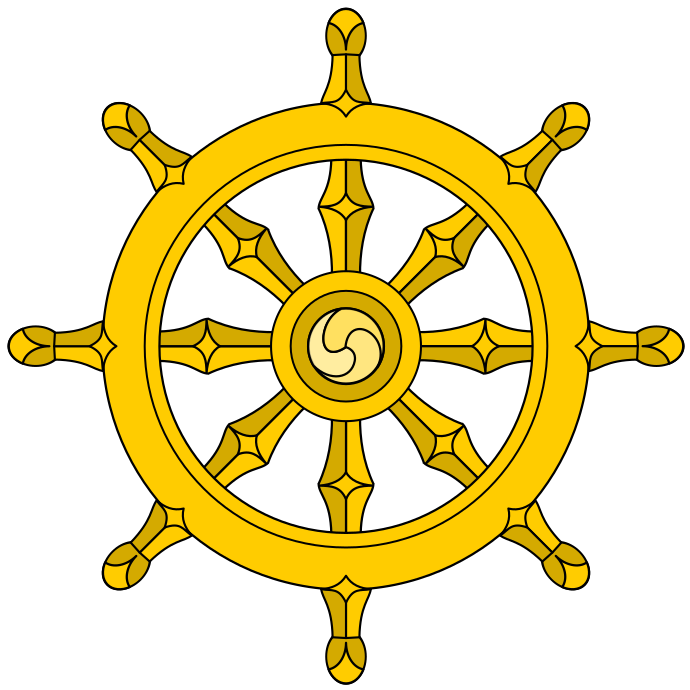













{{item.time}} {{item.replyListShow ? '收起' : '展开'}}评论 {{curReplyId == item.id ? '取消回复' : '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