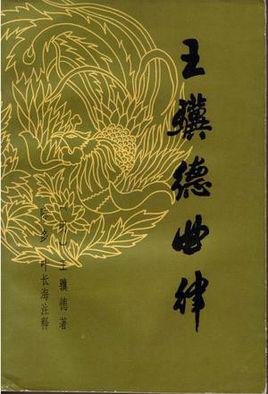论昆剧的战略继承
上世纪80年代、昆剧艺术界对昆剧展开了大规模的抢救工作,使清末“全福班”以来流传于世的大多数折子戏得到了继承,濒危的昆剧剧种也获得了新的生机。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昆剧列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指的正是当代昆剧界继承自“传”字辈等前辈艺术家的传世折子戏,大约200余出。
对200余出昆剧折子戏一招一式的传承是一种最基本的也是必不可少的技术件保护,有很高的战术意义。但作为“非物质遗产”的昆剧和一切有形的“物质遗产”在保护方式上显然有着质的区别。昆剧是一种有生命的艺术活体,纯粹的技术性继承最终不能真正地保护昆剧。我们过去关注较多的只是传统折子戏的抢救、积累、表演艺术的师承以及昆剧院团的硬件建设,对“非物质遗产”的保护方式还缺乏系统的宏观研究,即长期侧重于管理性保护,而在一定程度上疏忽了通过理论引导敦促昆剧的保护、继承超越战术的绳墨而进入战略的轨道。
昆剧继承的战略主体――昆剧观众
有人提倡“一字不改”地维护昆剧的“原汁原味”、担心昆剧的稍有创新会使联合国不再承认它的遗产资格,由是认定昆剧的任何创新都是“自杀”。与“自杀论”相呼应,还有人把昆剧没有观众归咎于当代观众文化水平低下,甚至还认为昆剧的价值就在于没有观众。这些观点乍一听可笑,幼稚到可以不屑一顾,然而,恰恰是这类“幼稚病”造成了当代昆剧人继承心理的巨大障碍。
昆剧的继承主体习惯上认定是其艺术的载体--从事表演艺术的演员,于是昆剧界在积极鼓励折子戏 传承的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同时,通过以继承主体为主导的各种方式,对观众进行“争取”、“培养”。然而,几十年来昆剧的窘境并没有多少改善。据初略统计,在昆剧的发样地苏州,多年举办“星期专场”,赠票演出折子戏,能自动进入剧场的观众不过百余人,这对于拥有六百万人口的大城市而言,简直难成比例。这种“争取观众”、“培养观众”实验的彻底失败,终于引发出了新的逆向思维命题--强调昆剧观众对昆剧传承的决定作用:剧种的盛衰并非取决于剧种对观众的争取培养,而恰恰相反,是观众对剧种的态度。观众才是戏剧艺术的创造者,也是艺术传承的主动力。历史也是这样演进的:昆剧最初应了士大夫和知识阶层这一特殊观众群的审美愿望而诞生,其后随着苏州资本主义萌芽经济的发展,昆剧面对新的观众结构,又按照新兴的市民阶层的要求改造了自己,从“典雅”趋向“雅俗共赏”。明代汤显祖不为魏良辅规定的曲律所拘泥;沈Z以“本色论”反对语言的典雅,他们同时表现出一种改革进取的智勇,仅仅是为了面对各自不同的观众阶层。到清代后期,昆剧在“花雅之争”中失利,不是昆剧的人才、艺术不如“花部”,恰恰是昆剧的观众移情别恋。与其说是昆曲远离了观众,不如说是观众抛弃了昆曲:这时的昆曲,完全丧失了鼎盛时期那种顺应观众潮流千方百计进行变革的胆识,一味抱残守缺,才终于越来越造成观众的大规模流失和剧种的急骤衰落。历史是如此,而另一方面,昆剧本体的表达,虽然要依靠演员的创造体验,但表演艺术家在舞台上的二度创造,必须在与观众的相互吸弓与互相反馈中才能真正实现。剧目在彩排时充其量是一种半成品,只有在剧场面对观众演出时,它才成为了艺术成品。因此,就昆剧本体的构成要素而言,不应该只包括文学、音乐、表演、舞台美术,还必须有观众。“自杀论”者排斥观众,否认观众在昆剧继承中的重要地位,他们不知道正是昆剧的观众才秉执大权、对昆剧折子戏乃至整个剧种进行着生杀予夺。
“自杀论”的一个出发点似乎是为了维护昆剧的传统,然而,昆剧的传统是什么?真正的昆剧传统是一种发展的传统,改革的传统,一种广采博纳、兼收并蓄以取悦观众的传统。号称“曲圣”、“鼻祖”的魏良辅以及明、清两代最著名的宗师大家如梁辰鱼、沈Z、汤显祖、李玉、叶堂之辈无不是改革大家。清末以来昆曲的急剧衰退,恰恰是因为昆剧丢失了自己最为重要的传统。关于这一点,其实古人比我们论述得更为透彻。如清代曲家徐大椿就说过这样的话:“如必字字句句皆求同于古人,一则莫可考究,二则难于传授。况古人之声,已不可迫,自吾作之……即便自成一家,亦仍真非方调也,“自杀论”是一种有害于昆曲生存的论调,它代表了创作源泉的彻底干涸和文艺活力的衰竭;它描绘的决不是昆曲今天的事实,这种论调最终将把本来少而又少的昆剧观众推得更远。“自杀论”对昆剧貌似敬恭,实质上从根本上否认了昆剧至今依旧是有生命的活体,否认只有创造才是昆剧的艺术灵魂和它的生命的渊薮。从而也否认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科学继承的基础。
近一二百年来,昆剧敝帚自珍,孤芳自赏,它虽然全力以赴打造了折子戏,然而,忽视观众的审美需求和拒绝求新创造的消极保护,却导致了折子戏以极为惊人的速度消亡,数以千计的折子戏到民国初叶只剩600余出,70年以后,即在当今只存下200多出--其中很多“冷戏”还处于随时消亡的高危状态。立足于战术继承的演出也许暂时可以满足少数昆曲遗老的审美情趣,但无法遏止折子戏的进一步消亡,因而,这类纯粹的技术性的保守继承绝没有出路。故当务之急,当从调查、测验观众心理着手,把昆剧观众引入昆剧的本体范畴,尽快建立和完善昆剧的“当代观众学”。在200多出折子戏一代又一代口传心授的基础上,再度恢复昆剧创新、发展的战略机制,以真正实现昆剧继承主体的战略位移。如任“幼稚病”蔓延,可演折子戏必将继续严重萎缩,遗产保护也将成为一句空话,这决不符合联合国把昆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本衷。
昆剧继承的战略思想――“八字方针”
艺术的受众始终领导着美学的时代潮流,审美对象总是在受众的视线内决定自己的方圆。19世纪的俄国哲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这样的话:“每一代的美都是而且也应该为那一代而存在,……当美与那一代同消逝的时候,再下一代将会有它自己的美、新的美,……今天能有多少美的享受,今天就给多少,明天是新的一天,有新的要求,只有新的美才能满足他们。”可见,迎合时代的审美潮流是一切美学形态在各个时代生存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古典戏剧艺术可以在当代得到保护、继承的一个内在活塞。
昆曲是明、清两代审美潮流的产物,昆曲的保护、继承必须通过对不同时代审美内涵的研究,以求得尽可能多的沟通点,这样才能保证保护、继承举措的有的放矢和有效性。上世纪20年代苏州昆剧传习所对危亡的昆剧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抢救与继承,然而,苏州昆剧传习所以来所有抢救、继承举措由于受继承思维的局限,并不能有效遏止折子戏的高速消亡。直到80年代文化部提出了“保护、继承、创新、发展”的“八字方针”、才为昆曲的科学保护、继承提供了理论指针。
“八字方针”立足于古今审美潮流的演变,运用先进的哲学观和文艺观,科学地揭示了古典戏剧艺术在当代的继承规律,它也包含了昆剧几个世纪中盛衰的一切经验与教训。“保护、继承”与“创新、发展”构成了一种矛盾统一的辩证关系,缺一不可。正是“八字方针”,它重新赋予了古老衰弱的昆剧以新的“吐故纳新”机制和向上、向前的“批判继承”精神。提到“批判”,人们常常心有余悸,其实,在任何艺术品面前,批判的心理总是“观众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观众的批判心理多数时候是非意识形态的,是一种直觉的、自然的,甚至是纯艺术的反应,紧紧维系于时代的审美潮流且受其左右。例如传奇《雷峰塔》中的白蛇形象,在原始的故事情节中是一个凶狠、残忍、的妖孽,在最初的昆剧传奇里,白蛇一方面被塑造成为追求真挚爱情,不惜离经叛道的形象,同时,剧作又从封建的正统观念出发,否定了白蛇的“合法”婚姻,并以白蛇被于雷峰塔下作结。过了30多年,白蛇在昆剧舞台上完全摆脱了妖气,成为一个温柔、多情、坚贞不屈而富于人性的正面形象,在民间艺人删编的演出本里,一度被“永镇雷峰塔”的悲剧角色,最后“生子得第”,还补给了她一个光明的结局。推动传奇情节不断演化的正是蕴藏在观众中的批判力量,这种无形的批判力量使得一个白蛇求爱的离奇故事,逐渐演化成为一种向封建礼教和封建秩序发起巨大冲击的力源,而倾向于“大团圆”的传奇结局模式,也正体现了对社会现实的某种共性的观众批判心理。这种观众批判心理才是传奇情节、人物乃至主题思想不断进化的原动力。批判继承,对于精华和糟粕的识别尽管各个时代有不同的标准,但最终将听命于“观众选择”。传奇《雷峰塔》的题材沿革,因紧吻着“观众选择”的轨迹不断推陈出新,才终于造就了一部不朽的传世名剧。
“推陈出新”乃是“八字方针”的灵魂。昆剧几百年的继承史,实际上是一部椎陈出新的发展史。有人提倡变昆剧为“博物馆艺术”,以为在相对真空的环境中才能不流失“正宗”,才是真正的“保护”,这不过一厢情愿罢了。这种“保护”或许可以保护少量常演的折子戏于一时,谈不上保护整个剧种。我们注意到,现在的“八字方针”--保护、继承、创新、发展与80年代所提的“八字方针”--抢救、继承、改革、发展,有了细微的区别。与之相比,则“创新”较“改革”更为精确,更强调了昆剧内在的推陈出新机制;“保护”比“抢救”也更现实,80年代以来,随着“传”字辈等前辈艺术家的陆续谢世,“抢救”任务顺理成章地要让位于“保护”。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只要昆剧推陈出新的机制尚未真正确立,大多数无观众(观众不爱看),无演员(演员不愿演)的“冷戏”就无法摧热,这批“冷戏”必然只集中在极少数人的身上,成了“传”字之后的抢救对象,故“抢救”的任务其实远没有结束。我们知道,大多数“传”字辈表演艺术家对艺术继承的过于保守都有着切肤之痛,他们在学传授折子戏的时候,总要对原来的内容和形式进行必要的剪裁、改造,作一些“推陈”的努力、“出新”的尝试。这也是对当代观众欣赏心理的一种尊重。“传”字辈表演艺术家王传淞曾对他的学生记过一句至理名言:“像我者死!”如果“传”字辈无视“口头遗产”传承的特殊性,拒绝推陈出新,只把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感谢每一位辛勤著写的作者,感谢每一位的分享。

相关资料
展开
- 有价值
- 一般般
- 没价值








推荐阅读
关于我们

APP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