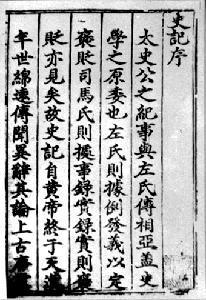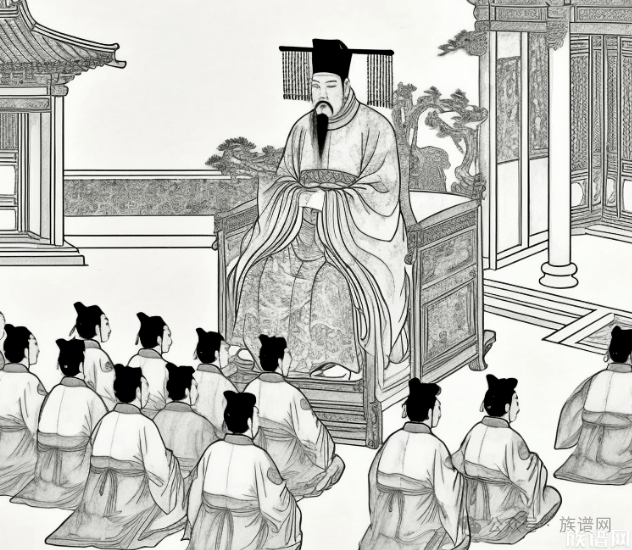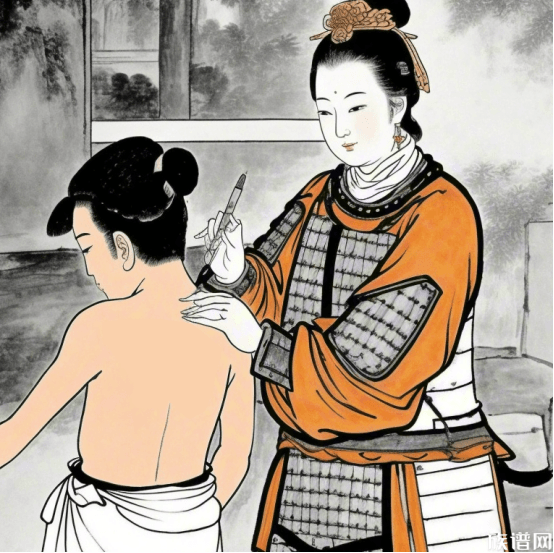齐鲁文化―鲁文化在中国上古文化中的地位
在中国上古时期,由于山川阻隔,交通极为不便。西周以来,以各个重要的诸侯封国为中心,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在众多的区域文化中,鲁国的文化居于一种领先的、中心的地位。
第一,鲁国受封之地早已经是中国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
山东被称为“齐鲁之邦”,先秦时期,鲁国和齐国分处于泰山南、北,在泰山以南(今鲁南)地区,已发现了众多的原始文化遗迹。“沂源人”与“北京人”时代相当,他们可能是这里古人类的祖先。以之为中心,仅其附近便发现了猿人化石和近百个旧石器和新石器地点,说明这里是几十万年以来古人类活动的重要中心之一。更为重要的是,进入新石器时代以来,这里更有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一脉相连,在鲁南地区形成了中国史前文化的完整序列。《帝王世纪》云:“炎帝自陈营都于鲁曲阜。黄帝自穷桑登帝位,后徙曲阜。少昊邑于穷桑,以登帝位,都曲阜。颛顼始都穷桑,都商丘。”张守节《史记正义》曰:“穷桑在鲁北,或云穷桑即曲阜也。又为大庭氏之故国,又是商奄之地。”远古时代许多氏族首领都与曲阜有关,这种现象不是偶然的。
周初,伯禽为首的周人来到曲阜一带后,这里又成为东西文化的交汇之地。殷商兴起于东方,曲阜一带曾为商人旧都,即使在迁殷之后,他们仍然与这里联系密切。直到周初,这里依然是殷商势力极重的地区。周族自西方发展起来,他们在取代殷商之后,要想很好地统治天下,就不能不把东方作为统治的重点,因此,可以说鲁国受封之地是他们首先要考虑的战略要地。这里距王都较远,东南沿海地区的淮夷以及徐戎等也没有立即臣服于周。武庚叛乱时,"殷东国五侯"群起叛乱,奄国及其附近各部都是周公东征的主要对象,史籍中所谓“攻商盖”、“攻九夷”(《韩非子・说林上》)、“灭国者五十”(《孟子・滕文公下》)都是在这些地区。甚至伯禽被封于曲阜后,“淮夷、徐戎及商奄又叛”(《艺文类聚》卷十二引《帝王世纪》)。欲很好地镇抚东方,把这里作为周室堡垒是非常合适的。
伯禽受封时,周室为鲁国制定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的治国方针,并分给鲁国“殷民六族”,使之“职事于鲁”(《左传》定公四年)。这样,伯禽一支所带来的周文化与殷遗民及当地土著固有的文化相互交汇、影响,共同形成鲁国的文化。
第二,鲁文化的特殊地位与鲁国在当时诸侯国中的特殊地位是统一的。
鲁国虽是周王朝分封的一个邦国,但它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邦国。鲁自周初始封,历西周、春秋、战国,到公元前249年为楚国所灭,历时七、八百年,在当时的政治、文化舞台上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鲁国的始封之君是周公的长子,而周公无论在帮助武王争夺天下,还是在成王年幼时平定天下以及辅助成王,都有卓著的功勋,他在周初政治中的地位十分显赫。因此,鲁国初封时不仅受赐丰厚,而且相对于他国来说还得到了不少特权。鲁国可以“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礼记・明堂位》也说:“凡四代之器、服、官,鲁兼用之。是故,鲁,王礼也,天下传之久矣。”从文献记载以及考古材料综合考察,这种记载应该是可信的。如周王室的职官“宗伯”、“太宰”、“大司徒”等,鲁即有之。如替国君掌管祭祀的“宗伯”,其他国家只称“宗”或“宗人”,有“宗伯”之称的只有周王室和鲁国。又,“鲁得立四代之学”(《礼记・明堂位》孔颖达疏),鲁还有四代之乐。恐怕这都是鲁国特有的现象。
鲁国受封的同时或者稍后,周王室在东方又分封了一些小国,这些小国有的即为鲁的附庸,有的则以鲁国为“宗国”。时至春秋王室衰微,礼坏乐崩之际,许多小国依然纷纷朝鲁,并且到鲁国学礼、观礼。在东方夷人势力较重的地区,鲁国始终不忘“尊尊而亲亲”的原则,使鲁国的政权一直掌握在“伯禽”之后的周人手中,鲁国较完整地保存着周礼,周代的礼宾传统深深地影响了鲁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如在政治方面,《礼记・明堂位》说:鲁国“君臣未尝相弑也,礼乐、刑法、政俗未尝相变也。天下以为有道之国,是故,天下资礼乐焉。”在诸侯国中,鲁国的政治是相对较为稳定的,因此鲁国也就成为各国学习的榜样。《左传》襄公十年说:“诸侯宋、鲁,于是观礼。”宋国保留的自是殷礼,鲁国保存的则是典型的周礼,即所谓“周礼尽在鲁矣”(《左传》昭公二年)。这样,鲁国为宗周在东方代表的形象更加突出,因为时人视礼为国家的根本,周礼似乎就是周王朝的象征。
春秋时期,“政由方伯”,但在各诸侯国会盟等的班次上,鲁国却位居前列。一般说来,“周之宗盟,异姓为后”(《左传》隐公十一年),鲁既为姬姓,又为周公之裔,故在诸侯位次序列中有“班长”(国语・鲁语上)之称,被列为首席。如春秋初年,齐遭北戎侵犯,齐向各国求助。在战后答谢诸侯时,齐国馈送粮饩给各国大夫时,齐请鲁国案班次代为分派;晋文公主持“践土之盟”时,在各会盟国进行的歃血仪式次序上,除主盟的晋国外,鲁也被排在各国的最前面。既然周室对鲁国寄予厚望,把鲁国分封在商奄旧地,那么,在推行周代礼乐制度时,有“望国”地位的鲁国也就不能不以表率自居了。
鲁国为东方的宗周模式,担负着传播宗周礼乐文明的使命,如在周王朝治国政策的贯彻上,鲁国即堪为典范。周公治国,他的保民思想、明德慎罚、勤政任贤等都似乎在鲁国当政者身上有明显体现。当然,说鲁国为“宗周模式”,决不是说鲁国完全排除它的文化因素,使鲁国全盘周化,而是在政治统治上鲁国为周王朝的东方代理人,而且在鲁国上层贵族中完整地保存着周代礼制。事实上,鲁国要彻底推行周文化而以之取代当地的固有文化,既无必要,也没可能,因为周灭商后对殷商旧地采取的就是“怀柔”的政策,更何况鲁地殷遗势力极重,而且文化的推广也不是任何外来强力所能成功的。
第三,从与其他区域文化的比较中也能看出鲁文化在当时的重要地位。
在区域文化的研究中,人们往往将鲁文化与齐文化相互比较,这是很有道理的。齐、鲁两国地域相邻,在文化方面具有很多的可比之处。就先秦时期两国的文化而言,它们有同有异。从实质上说,崇周礼、重教化、尚德义、重节操等等都是两地人民共有的风尚。两国文化上的不同之处更多,齐人的务实开放,鲁人的重视礼乐,使齐、鲁两国在文化上各具特色,并且位居当时华夏文化的领先或者中心地位。但齐、鲁两国的文化孰优孰劣,不少论者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大谈鲁文化的所谓“保守”、“落后”和“缺乏进取”。而实际上,分析文化的优劣应当具有历史的眼光,而不应该离开当时的具体时代。
从文化的传承关系上看,周文化与鲁文化乃一脉相承,或者说鲁文化就是周文化的代表。周人灭商以来,周文化在总结和吸纳前代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又有了显著进步。《礼记・表记》上说:“夏道尊命,事鬼敬神”,“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有学者称夏、商时期的文化分别为“尊命文化”和“尊神文化”。从根本上说,周文化就是礼乐文化,而礼乐的实质则是秩序,礼乐文化是一种人文文化。周文化与夏、商文化的不同,最为重要的即在于其人文理念的上升。自周公制礼作乐开始,周文化的重礼风格便已初步形成,而周人又有重视农业的传统与之相适应,这样,便奠定了中国几千年传统宗法农业社会的文化基础。
鲁国的文化风格与周文化是一致的。建国伊始,鲁国的始封之君伯禽就在鲁地变俗革礼,进行大的动作,推行一种新文化。应当指出,鲁国的这种变革历时三年,显然是循序渐进,而非急风暴雨一般。因此,它与强行毁灭一种文化而推行另一种文化是有区别的。其实,周代礼乐广采博纳,其中也有殷文化的不少因素,因为周礼即是从殷礼“损益”而来。应当承认,在与周边当时各族的文化相比,周文化是一种最为先进的文化。鲁国下了大的气力推行周文化,是为了适应周王朝的政治统治。从一开始,鲁人便显示了文化上的进取精神。
文化的优劣在文化的交流中最容易看得清楚。一般说来,落后的文化要不断地学习先进的文化,来丰富和完善自身。就齐、鲁两国而言,齐国就常常向鲁国学习。
众所周知,管仲的改革对于齐国成为泱泱大国具有关键性的意义。但是,正如有的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管仲改革乃有吸收鲁文化之长、补齐文化之短的深意。管仲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便是定四民之居,推行士、农、工、商四业并举的政策,把发展农业放在经济基础的地位,置于工、商业之前,这明显吸收了鲁国以农业立国的思想,以补齐国偏重工商、渔盐、女工之业,忽视农业而造成社会不稳之弊端;管仲还针对齐国传统礼义道德观念淡薄,习俗落后,以致于君臣上下无礼、男女关系混乱,从而严重影响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的情况,十分注意从鲁国吸收周礼文化,强调礼义道德的建设。
管仲如此,齐国的其他君臣何尝不是如此。齐国虽然有人对孔子所讲的繁文缛礼不感兴趣,但他们毕竟不能不对鲁国“尊卑有等,贵贱有序”礼治秩序表示重视。例如,齐国的另一位名相晏婴就曾经与齐景公一起到鲁国“俱问鲁礼”(《史记・齐太公世家》);孔子到齐国时,齐景公也不失时机地问政于孔子。又如,鲁国发生之乱时,齐欲伐鲁,但有人看到鲁国“犹秉周礼”,认为“鲁不弃周礼,未可动也”(《左传》闵公二年)。有一次,齐人伐鲁,见一妇人带着两个孩子,开始时抱小而挈大,大军将要到跟前时,反而抱大而挈小。当问及时,妇人说:“大者,妾夫兄之子;小者,妾之子。夫兄子,公义也;妾之子,私爱也。宁济公而废私耶。”齐国从而罢军,他们认为:“鲁未可攻也,匹夫之义尚如此,何况朝廷之臣乎?”(《说苑疏证・佚文考》)
齐人看重周礼,向鲁国借鉴、学习,显示了其积极进取、灵活开放的一面,这当然是值得肯定的。然而,这也证明齐文化中存在不少有待改进之处。如在君臣关系方面,齐国出现了不少相弑相残的现象,而鲁国的情况要好得多。鲁国的大夫臧文仲曾教别人“事君之礼”说:“见有礼于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养父母也;见无礼于其君者,逐之,如鹰之逐雀也。”(《左传》文公八年)这种典型的尊君之论,便基于鲁国深沉的礼乐传统,这对于鲁国君臣关系的和睦,对于鲁国社会的安定都有积极的作用。而且动态地就君主制度的发展来看,鲁国的这种礼治秩序也有其进步的一面。再如婚嫁习俗方面,“同姓不婚”是鲁国最为基本的婚姻习俗,不论男婚还是女嫁,均不找同姓。鲁国还特别注重男、女之别和夫、妻之别,这与齐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婚姻制度史的研究早已表明,“同姓不婚”之制相对于氏族族内婚姻是极大 的进步。正因如此,鲁国的婚姻制度才为当时各国所普遍认可,例如,《史记・商君列传》记商鞅说:“如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为男、女之别,大筑冀阙,营如鲁、卫矣。”在当时的情况下,严格的婚姻制度以及男女界限是清除旧的习俗的最好办法,在这方面,鲁人的做法是具有表率作用的。
齐、鲁两国的文化交流从各自的文化特色形成之日起便开始了,但两国文化上的优劣之争似乎也未间断,直到战国时的孟子也还如此。《孟子・公孙丑上》记公孙丑问孟子说:“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婴之功,可复许乎?”孟子回答说:“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婴而已矣。”孟子的话就似乎表现了鲁人对齐人的轻蔑。其实,由于齐文化的起点较低,齐人在以后的国家建设与发展中努力进取,使齐文化表现出了开阔、灵活、积极的特质。所以清代学者俞樾在谈到齐人对于后来儒学发展所起的作用时说到:“齐实未可轻也”(《湖楼笔谈》卷二)。通过近10年来的深入研究,人们加深了对齐文化的认识,从而已经改变了长期以来对齐文化的不恰当评价。
最后,还有必要谈一谈“鲁文化”与所谓“邹鲁文化”的概念问题。
我们前面引到孟子的话,认为他的观点代表了鲁人看法,但并不是说孟子也是鲁人。关于孟子的里籍,《史记》称其为邹人。邹地战国时是否属鲁,历来存有争议。但不论如何,孟子和鲁国的联系却不同寻常:首先,孟子居地近鲁。他本人曾说自己“近圣人(孔子)之居若此之甚也”(《孟子・尽心下》);孟子又为鲁国孟孙氏之裔;孟子在齐,丧母而归葬于鲁,说明孟子上代迁鲁不久;孟子还极为崇拜孔子,并“受业子思之门人”,其思想与鲁文化传统的关系不可分割。因此,认为孟子的观点代表了鲁人的看法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孟子为邹人,以孟子和儒家在当时的巨大影响,人们自然不能忽略作为一个具体国家的邹国。邹国就是邾国,在春秋时,“邾”有两种读音,《公羊传》读为邾娄,《左传》读为邾,对此,王献堂先生解释说:“古人音读有急声,有漫声,急声为一,漫声为二,而其漫声之二音,亦可分读。......漫声连举为邾娄,急声单举为邹,漫声分举,则为邾为娄。”(《邾分三国考》)王献堂先生的意见是正确的。这就是说,战国时代邾国被称为邹,只是称呼了邾娄的合音。
邾国立国较早,周朝灭商后,又封曹侠于邾,邾国遂成为周王朝的一个诸侯国。邾国的北部边境与鲁国国都曲阜相距很近,邾君曾言“鲁击柝闻于邾”(《左传》哀公七年),春秋后期,“邾庶以其漆、闾丘奔鲁”(《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邾国的北部边境逐渐南移。这样,孟子居地与鲁国的联系更加密切。
邾为曹姓国家,从意识形态方面的文化看,邾国受周礼的影响很少。如邾人用人殉葬,用人祭社,这都不符合周礼的要求。鲁人就称邾人为“夷”,邾、鲁两国文化差异较大。只是到了战国时代,由于鲁国儒家文化的影响,如孔子的孙子子思曾到邹地讲学,特别是孟子迁居到邹,使邹地名声日隆,这里也有了浓重的儒家文化氛围。在这一点上,人们才将邹地与鲁国相提并论,而且,由于孟子的原因,自战国时起,人们将两地合称时,还把“邹”放在“鲁”的前面,而称为“邹鲁”。因此,将鲁文化作为周代的区域文化进行研究,而不是专门探讨作为一个学术派别的儒家文化时,还是以“鲁文化”(而不是“邹鲁文化”)作为一个研究单元为宜。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感谢每一位辛勤著写的作者,感谢每一位的分享。

相关资料

- 有价值
- 一般般
- 没价值








24小时热门
推荐阅读
关于我们

APP下载